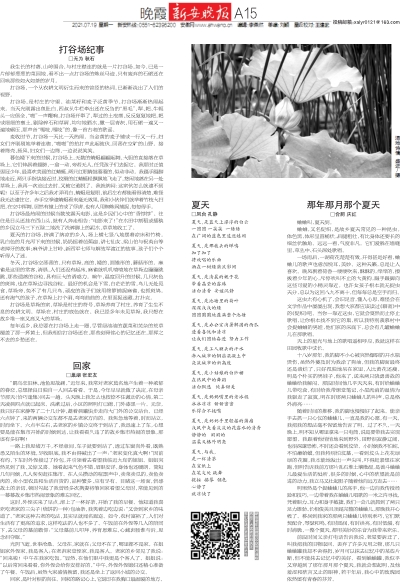发布日期:
打谷场纪事
□无为秋石
我生长的村落,山岭围合,与村庄襟连的就是一片打谷场,如今,已是一片郁郁葱葱的菜园地,看不出一点打谷场的蛛丝马迹,只有废弃的石磙还在回味那些如火如荼的岁月。
打谷场,一个从农耕文明衍生而来的曾经的热词,已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打谷场,是村庄的守望。油菜籽和麦子泛黄季节,打谷场渐渐热闹起来。当天光刚露出鱼肚白,四叔从牛栏牵出还在反刍的“黑毛”,犁、耙、牛轭头一应俱全,“啪”一声鞭响,打谷场开犁了,犁过的土疙瘩,反反复复地耙,耙成细细的壅土,剔除碎石和草屑,均匀地晒水,撒一层青灰,用石磙一遍又一遍地碾压,那声音“嘎吱,嘎吱”的,像一首古老的歌谣。
麦收时节,打谷场一天比一天热闹。当金黄的麦子铺成一行又一行,妇女们齐刷刷地举着连枷,“啪啪”的拍打声此起彼伏,回荡在空旷的山野。接着筛壳、扬风,妇女们一边筛,一边说说笑笑。
暮色矮下来的时候,打谷场上,无数的蜻蜓翩翩起舞,大胆的直接落在草垛上,它们伸展着翅膀,一翕一动,旁若无人,任凭孩子们去捉它。我那时正值弱冠少年,最喜欢美丽的红蜻蜓,两只红眼睛鼓溜溜的,似动非动。我蹑手蹑脚地走近,两只手指快接近时,狡猾的红蜻蜓轻飘飘地飞走了,悠闲地落在另一处草垛上,我再一次追过去时,又被它逃脱了。我就纳闷:这家伙怎么就逮不到呢?以至于许多年之后我才弄明白,蜻蜓是复眼,前后左右都能看得清楚,难怪我无法逮住它。赤手空拳逮蜻蜓看来毫无效果,我和小伙伴们就举着竹枝大扫把,在空中挥舞,居然有撞上的成了俘虏,也有人用蜘蛛网捕捉,每每得手。
打谷场最热闹的时候当数放露天电影,这是乡民们心中的“香饽饽”。往往是日头还挂在西山头,就有人奔走相告:“电影来了!”在水田中割稻或插秧的乡民立马三下五除二地洗了洗裤脚上的泥水,草草地收工了。
夏天的打谷场,挤满了纳凉的乡人,场上横七竖八地摆着凉床和竹椅。乳白色的月光泻下来的时候,奶奶摇着芭蕉扇,讲七仙女、梁山伯与祝英台等老掉牙的故事;麻爷讲上甘岭、新四军七师与解放军渡江的故事,孩子们个个听得入了迷。
冬天,打谷场空荡荡的,只有草垛,高的,矮的,圆锥形的,蘑菇形的。麻雀是这里的常客,清晨,人们还没有起床,麻雀就叽叽喳喳地在草垛边蹦蹦跳跳,那些遗落的谷粒,具有巨大的诱惑力。晌午,温度回升的时候,几只灰色的斑鸠,也在草垛边寻找谷粒。最好的机会是下雪,白茫茫的雪,鸟儿无处觅食,草垛旁,免不了有几只鸟,顽皮的孩子们就用筛箩捕捉麻雀,也抓斑鸠。还有淘气的孩子,在草垛上打个洞,弯弯曲曲的,在里面捉迷藏、打扑克。
打谷场是草垛的家,草垛是村庄的符号,草垛养育了村庄,养育了生生不息的农耕文明。草垛在,村庄的底色就在。我已经多年未见草垛,我只想在故乡堆一座又高又大的草垛。
每年返乡,我总要在打谷场上走一圈,尽管绿油油的蔬菜和芜杂的荒草覆盖了那一抔黄土,但我相信打谷场还在,那些刻骨铭心的记忆还在,那挥之不去的乡愁还在。
我生长的村落,山岭围合,与村庄襟连的就是一片打谷场,如今,已是一片郁郁葱葱的菜园地,看不出一点打谷场的蛛丝马迹,只有废弃的石磙还在回味那些如火如荼的岁月。
打谷场,一个从农耕文明衍生而来的曾经的热词,已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打谷场,是村庄的守望。油菜籽和麦子泛黄季节,打谷场渐渐热闹起来。当天光刚露出鱼肚白,四叔从牛栏牵出还在反刍的“黑毛”,犁、耙、牛轭头一应俱全,“啪”一声鞭响,打谷场开犁了,犁过的土疙瘩,反反复复地耙,耙成细细的壅土,剔除碎石和草屑,均匀地晒水,撒一层青灰,用石磙一遍又一遍地碾压,那声音“嘎吱,嘎吱”的,像一首古老的歌谣。
麦收时节,打谷场一天比一天热闹。当金黄的麦子铺成一行又一行,妇女们齐刷刷地举着连枷,“啪啪”的拍打声此起彼伏,回荡在空旷的山野。接着筛壳、扬风,妇女们一边筛,一边说说笑笑。
暮色矮下来的时候,打谷场上,无数的蜻蜓翩翩起舞,大胆的直接落在草垛上,它们伸展着翅膀,一翕一动,旁若无人,任凭孩子们去捉它。我那时正值弱冠少年,最喜欢美丽的红蜻蜓,两只红眼睛鼓溜溜的,似动非动。我蹑手蹑脚地走近,两只手指快接近时,狡猾的红蜻蜓轻飘飘地飞走了,悠闲地落在另一处草垛上,我再一次追过去时,又被它逃脱了。我就纳闷:这家伙怎么就逮不到呢?以至于许多年之后我才弄明白,蜻蜓是复眼,前后左右都能看得清楚,难怪我无法逮住它。赤手空拳逮蜻蜓看来毫无效果,我和小伙伴们就举着竹枝大扫把,在空中挥舞,居然有撞上的成了俘虏,也有人用蜘蛛网捕捉,每每得手。
打谷场最热闹的时候当数放露天电影,这是乡民们心中的“香饽饽”。往往是日头还挂在西山头,就有人奔走相告:“电影来了!”在水田中割稻或插秧的乡民立马三下五除二地洗了洗裤脚上的泥水,草草地收工了。
夏天的打谷场,挤满了纳凉的乡人,场上横七竖八地摆着凉床和竹椅。乳白色的月光泻下来的时候,奶奶摇着芭蕉扇,讲七仙女、梁山伯与祝英台等老掉牙的故事;麻爷讲上甘岭、新四军七师与解放军渡江的故事,孩子们个个听得入了迷。
冬天,打谷场空荡荡的,只有草垛,高的,矮的,圆锥形的,蘑菇形的。麻雀是这里的常客,清晨,人们还没有起床,麻雀就叽叽喳喳地在草垛边蹦蹦跳跳,那些遗落的谷粒,具有巨大的诱惑力。晌午,温度回升的时候,几只灰色的斑鸠,也在草垛边寻找谷粒。最好的机会是下雪,白茫茫的雪,鸟儿无处觅食,草垛旁,免不了有几只鸟,顽皮的孩子们就用筛箩捕捉麻雀,也抓斑鸠。还有淘气的孩子,在草垛上打个洞,弯弯曲曲的,在里面捉迷藏、打扑克。
打谷场是草垛的家,草垛是村庄的符号,草垛养育了村庄,养育了生生不息的农耕文明。草垛在,村庄的底色就在。我已经多年未见草垛,我只想在故乡堆一座又高又大的草垛。
每年返乡,我总要在打谷场上走一圈,尽管绿油油的蔬菜和芜杂的荒草覆盖了那一抔黄土,但我相信打谷场还在,那些刻骨铭心的记忆还在,那挥之不去的乡愁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