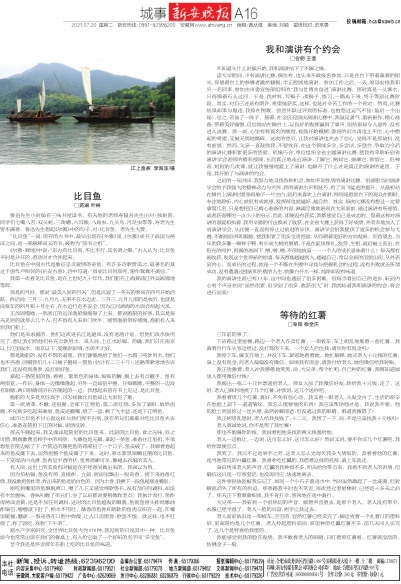发布日期:
比目鱼
□芜湖叶裕
鲁迅先生小时侯在三味书屋读书。有天他的老师寿镜吾先生出对:独角兽。同学们七嘴八舌:双头蛇、三角蟾、六耳猴、八角虫、九头鸟、百足虫等等,寿老先生皆不满意。鲁迅先生想起《尔雅》中的句子,对:比目鱼。老先生大赞。
“比目鱼”一词,现存的古书中,最早出现在《尔雅》里。《尔雅》成书于战国与两汉之间,是一部解释词义的书,被称为“辞书之祖”。
《尔雅·释地》中说:“东方有比目焉,不比不行,其名谓之鲽。”古人认为,比目鱼平时是分开的,游动时才合并起来。
比目鱼在中国古代是象征忠贞爱情的奇鱼。有许多诗歌赞美之,最著名的莫过于唐代卢照邻的《长安古意》,诗中写道:“得成比目何辞死,愿作鸳鸯不羡仙。”
我第一次看见比目鱼,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我们船在上海黄浦江外吴淞锚地等卸。
那是四月份。都说“最美人间四月天”,但是沉寂了一冬天的季风在四月开始活跃。俗话说:三月三、九月九,无事不在水边走。三月三、九月九指的是农历,也就是说每年的四月和十月左右,在水边行走不安全,因为江河湖海的水面会刮起大风。
正加固缆绳,一条浙江的远洋渔船缓缓靠了上来。都说跑船的好客,其实是每天见到的就那么几个人,巴不得有人来串门吹牛。刚帮渔船带好缆绳,渔船有人来到我们船上。
他们是来求援的。他们这次进长江是避风,没有进港计划。但他们淡水快用完了,想让我们给他们补充点饮用水。来人说,上江水好喝。的确,我们只在南京以上江里取水。南京以下,受潮汐影响,水质不太好。
都是跑船的,没有不帮的道理。我们慷慨地给了他们一水箱三吨饮用水,他们也不吝啬,回赠我们几十只梭子蟹和一筐鱼(估计有二三十斤),还略带歉意地告诉我们,还没有到渔季,没打到好鱼。
拿起一条筐里的鱼,看看。紫黑色的身体,细细的鳞,摸上去有点戳手。鱼有两指宽,一拃长,身体一边微微隆起,另外一边却很平整。仔细瞧瞧,平整的一边没有眼睛,两只眼睛同时长在隆起的一边。我想起来曾在书上见过,是比目鱼。
跑船的大多是烹饪高手,可怎样做比目鱼却让大家犯了难。
第一次清蒸,不嫩,还很腥,全部下江喂鱼;第二次红烧,多加了调料,依然很腥,不光刺多吃起来麻烦,鱼皮还戳嘴,烧了一盆,剩了大半盆,还是下江喂鱼。
或许比目鱼不甘心就这样与我们挥手告别,就在弟兄们渐渐对吃比目鱼失去信心,准备连筐扔下江的时候,剧情反转。
那天午睡起来,我又端详起筐里的比目鱼来。此刻的比目鱼,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倒真像曹丞相手中的鸡肋。大概也是无聊,拿起一条鱼,准备往江里扔,不承想鱼在筐边剐了下,竹筐边的篾把鱼的背部拉了一个口子,鱼皮破了。我顺着卷起来的鱼皮撕下去,居然把整个鱼皮撕了下来。这时,原本紫黑细鳞丑陋的比目鱼,一下变得洁白光滑,鱼肉呈半透明状,鱼骨清晰可见,像褪去衣服的美人。
有人说,这世上的美食有时候是在不经意间做出来的。我深以为然。
因为怕粘锅,鱼没有煎,直接炸。立刻,厨房里飘出一股奇香。接下来准备红烧,我没敢把鱼炸老,炸出来的鱼是奶白色的。因为太香,我揪下一段鱼尾塞进嘴里。
刚吃到嘴里的鱼酥脆爽口,嚼了几下又感觉绵软悠长,没有加任何调料,却没有半丝腥味。香味叫醒了弟兄们,尝了以后都说要稍微炸老点。我依计而行,鱼炸得两面金黄,还是不加任何调料,这时的比目鱼越发的酥脆,鱼刺鱼骨头炸得像油炸锅巴,嚼嚼就下肚了,根本不用吐。酥香的鱼骨和绵软的鱼肉交织在一起,在嘴里碰撞、翻滚,一股奇香在口腔中弥漫,让人口齿留香,欲罢不能。就这样,也不红烧了,炸了就吃,戏称“下午茶”。
据水产学家研究,全世界比目鱼大约570种,我见到的只是其中一种。比目鱼如今也常常出现在我们的餐桌上,有人给它取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叫“多宝鱼”。
至今我还是怀念那年在船上吃的比目鱼的味道。
鲁迅先生小时侯在三味书屋读书。有天他的老师寿镜吾先生出对:独角兽。同学们七嘴八舌:双头蛇、三角蟾、六耳猴、八角虫、九头鸟、百足虫等等,寿老先生皆不满意。鲁迅先生想起《尔雅》中的句子,对:比目鱼。老先生大赞。
“比目鱼”一词,现存的古书中,最早出现在《尔雅》里。《尔雅》成书于战国与两汉之间,是一部解释词义的书,被称为“辞书之祖”。
《尔雅·释地》中说:“东方有比目焉,不比不行,其名谓之鲽。”古人认为,比目鱼平时是分开的,游动时才合并起来。
比目鱼在中国古代是象征忠贞爱情的奇鱼。有许多诗歌赞美之,最著名的莫过于唐代卢照邻的《长安古意》,诗中写道:“得成比目何辞死,愿作鸳鸯不羡仙。”
我第一次看见比目鱼,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我们船在上海黄浦江外吴淞锚地等卸。
那是四月份。都说“最美人间四月天”,但是沉寂了一冬天的季风在四月开始活跃。俗话说:三月三、九月九,无事不在水边走。三月三、九月九指的是农历,也就是说每年的四月和十月左右,在水边行走不安全,因为江河湖海的水面会刮起大风。
正加固缆绳,一条浙江的远洋渔船缓缓靠了上来。都说跑船的好客,其实是每天见到的就那么几个人,巴不得有人来串门吹牛。刚帮渔船带好缆绳,渔船有人来到我们船上。
他们是来求援的。他们这次进长江是避风,没有进港计划。但他们淡水快用完了,想让我们给他们补充点饮用水。来人说,上江水好喝。的确,我们只在南京以上江里取水。南京以下,受潮汐影响,水质不太好。
都是跑船的,没有不帮的道理。我们慷慨地给了他们一水箱三吨饮用水,他们也不吝啬,回赠我们几十只梭子蟹和一筐鱼(估计有二三十斤),还略带歉意地告诉我们,还没有到渔季,没打到好鱼。
拿起一条筐里的鱼,看看。紫黑色的身体,细细的鳞,摸上去有点戳手。鱼有两指宽,一拃长,身体一边微微隆起,另外一边却很平整。仔细瞧瞧,平整的一边没有眼睛,两只眼睛同时长在隆起的一边。我想起来曾在书上见过,是比目鱼。
跑船的大多是烹饪高手,可怎样做比目鱼却让大家犯了难。
第一次清蒸,不嫩,还很腥,全部下江喂鱼;第二次红烧,多加了调料,依然很腥,不光刺多吃起来麻烦,鱼皮还戳嘴,烧了一盆,剩了大半盆,还是下江喂鱼。
或许比目鱼不甘心就这样与我们挥手告别,就在弟兄们渐渐对吃比目鱼失去信心,准备连筐扔下江的时候,剧情反转。
那天午睡起来,我又端详起筐里的比目鱼来。此刻的比目鱼,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倒真像曹丞相手中的鸡肋。大概也是无聊,拿起一条鱼,准备往江里扔,不承想鱼在筐边剐了下,竹筐边的篾把鱼的背部拉了一个口子,鱼皮破了。我顺着卷起来的鱼皮撕下去,居然把整个鱼皮撕了下来。这时,原本紫黑细鳞丑陋的比目鱼,一下变得洁白光滑,鱼肉呈半透明状,鱼骨清晰可见,像褪去衣服的美人。
有人说,这世上的美食有时候是在不经意间做出来的。我深以为然。
因为怕粘锅,鱼没有煎,直接炸。立刻,厨房里飘出一股奇香。接下来准备红烧,我没敢把鱼炸老,炸出来的鱼是奶白色的。因为太香,我揪下一段鱼尾塞进嘴里。
刚吃到嘴里的鱼酥脆爽口,嚼了几下又感觉绵软悠长,没有加任何调料,却没有半丝腥味。香味叫醒了弟兄们,尝了以后都说要稍微炸老点。我依计而行,鱼炸得两面金黄,还是不加任何调料,这时的比目鱼越发的酥脆,鱼刺鱼骨头炸得像油炸锅巴,嚼嚼就下肚了,根本不用吐。酥香的鱼骨和绵软的鱼肉交织在一起,在嘴里碰撞、翻滚,一股奇香在口腔中弥漫,让人口齿留香,欲罢不能。就这样,也不红烧了,炸了就吃,戏称“下午茶”。
据水产学家研究,全世界比目鱼大约570种,我见到的只是其中一种。比目鱼如今也常常出现在我们的餐桌上,有人给它取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叫“多宝鱼”。
至今我还是怀念那年在船上吃的比目鱼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