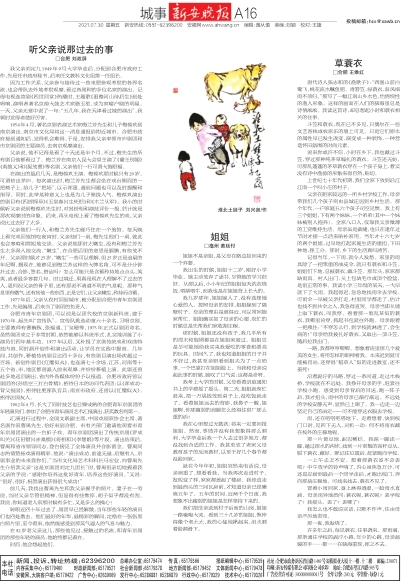发布日期:
听父亲说那过去的事
□合肥刘政屏
我父亲刘定九1949年9月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合肥市政府工作,先是任市政府秘书,后来任文教科文化组第一任组长。
因为工作关系,父亲参与接待过一些来肥参观考察的各界名流,也会带队去外地考察观摩,看过各剧种的多位名家的演出。记得电视连续剧《四世同堂》热播时,主题歌《重整河山待后生》到处唱响,演唱者著名京韵大鼓艺术家骆玉笙,成为家喻户晓的明星。一天,父亲无意中说了一句:“五几年,我在天津看过她的演出”,我顿时觉得老爸好厉害。
1954年4月,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先生和儿子梅葆玖到南京演出,南京市文化局将这一消息通报给附近城市。合肥市政府接到通知后,觉得机会难得,于是,安排我父亲率领市庐剧团和市京剧团的主要演员,去南京观摩演出。
父亲说,他不记得是看了十天还是半个月,不过,梅先生的所有剧目他都看过了。梅兰芳在南京人民大会堂主演了《霸王别姬》《英雄义》和《捉放曹》等名剧,父亲他们一行可谓大饱眼福。
在演出的最后几天,是梅葆玖主演。梅葆玖那时候只有20岁,可谓初出茅庐。每次演出时,梅兰芳先生都会坐在戏台侧面的一把椅子上,给儿子“把场”,以示郑重,遇到问题也可以及时提醒和指导。同时,此举某种意义上也是为儿子聚拢人气。梅葆玖演出的剧目有《四郎探母》《玉堂春》《生死恨》和《木兰从军》。我小的时候听父亲说到梅葆玖先生时,对其扮相和演技评价一般,估计就是那次观摩时的印象。后来,再从电视上看了梅葆玖先生的戏,父亲说比过去好了太多。
父亲他们一行人,和梅兰芳先生碰巧住在一个旅馆。每天晚上看完戏回旅馆吃夜宵时,父亲他们一桌,梅先生他们一桌,彼此也会寒暄和简短地交谈。父亲说他那时太嫩生,没有和梅兰芳先生太多深入地交流。“嫩生”,在合肥话里的意思是腼腆、有些放不开。父亲那时候才25岁,“嫩生”一些可以理解,但25岁正是追星的年纪啊,搁现在,能够见到梅兰芳这样的大牌名角,可不是分分钟扑过去,合影、签名、搭讪吗?怎么可能只是含蓄矜持地点点头、笑笑,或者最多客套几句。时过境迁,果真是现在人理解不了过去的人,更何况父亲的骨子里,还有那说不清道不明的气息呢。那种气息里有傲气,还有其他一些东西,正是它们,让父亲嫩生、矜持而含蓄。
1977年后,父亲从农村回到城市,被分配到合肥市青年京剧团工作,先是编剧,后来当了剧团的负责人。
合肥市青年京剧团,可以说是以团代校的京剧新科班,建于1970年,起先叫“宣传队”。宣传队挑选幼童六十余名,习唱京剧。主要教师有曹畹秋、张福通、丁宝珊等,1975年正式以剧团命名。虽然剧团成立于非常时期,依然能够以科班形式,扎实地训练了小演员们四年基本功。1977年以后,又补授了京剧传统戏和戏曲特技内容,同时展开创作和演出活动,让学员在实践中提高。几年间,共创作、移植传统剧目达四十多台,有些剧目演出场次超过一百场。新创作剧目《红缨似火》,也连演七十余场,江苏、河南等十五个省、市、地区都曾派人前来观摩,并纷纷移植上演。此剧还曾赴多地巡回演出,省内外各媒体纷纷予以报道。合肥市政府曾以剧团的《孙悟空三打白骨精》,招待日本的访问代表团;以《郑成功·背父报国》,招待驻肥部队官兵;南京市政府,还曾以《红缨似火》,招待法国友人。
1982年8月,长大了同时技艺也日臻成熟的合肥青年京剧团的年轻演员们,参加了合肥市青年演员艺术汇报演出,获奖数名列第一。
汇演进行过程中,全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著名剧作家曹禺先生,恰好来到合肥。市有关部门邀请他观看市青年京剧团演出的一台折子戏。青年京剧团演出了传统京剧《罗成叫关》《花田错》《赤桑镇》《将相和》《李慧娘》等片段。演出结束后,曹禺和省市领导同志,登台接见了全体演员并合影留念。曹禺同志热情赞扬戏演得精彩,他说:“演出成功,前途无量,后继有人,京剧事业的未来靠你们。”当市文化局艺术科科长马宏业,向曹禺先生介绍我父亲“这是京剧团刘定九团长”时,曹禺很亲切地握着我父亲的手说:“感谢你培养这批好青年,培养这些好演员。”又说:“很好,很好,祝贺演出获得很大成功!”
前几天,我找出曹禺先生和我父亲握手的照片。妻子在一旁说,当时父亲尽管很精神,但显得有些憔悴,胡子似乎都没有刮。我说,你知道老人家那时候有多忙,又是多么的操心?
转眼近四十年过去了,剧团早已经解散,当年那些年轻的演员们也四处散去。他们最好的年华,最精彩的瞬间,定格在一张张黑白照片里,至今看来,依然能感受到那英气逼人的气息与魅力。
在92岁老父亲这儿,那些他见过、接触过的名流,和青年京剧团的那些年轻的演员,他始终都记着在。
时而,他会想起他们。
我父亲刘定九1949年9月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合肥市政府工作,先是任市政府秘书,后来任文教科文化组第一任组长。
因为工作关系,父亲参与接待过一些来肥参观考察的各界名流,也会带队去外地考察观摩,看过各剧种的多位名家的演出。记得电视连续剧《四世同堂》热播时,主题歌《重整河山待后生》到处唱响,演唱者著名京韵大鼓艺术家骆玉笙,成为家喻户晓的明星。一天,父亲无意中说了一句:“五几年,我在天津看过她的演出”,我顿时觉得老爸好厉害。
1954年4月,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先生和儿子梅葆玖到南京演出,南京市文化局将这一消息通报给附近城市。合肥市政府接到通知后,觉得机会难得,于是,安排我父亲率领市庐剧团和市京剧团的主要演员,去南京观摩演出。
父亲说,他不记得是看了十天还是半个月,不过,梅先生的所有剧目他都看过了。梅兰芳在南京人民大会堂主演了《霸王别姬》《英雄义》和《捉放曹》等名剧,父亲他们一行可谓大饱眼福。
在演出的最后几天,是梅葆玖主演。梅葆玖那时候只有20岁,可谓初出茅庐。每次演出时,梅兰芳先生都会坐在戏台侧面的一把椅子上,给儿子“把场”,以示郑重,遇到问题也可以及时提醒和指导。同时,此举某种意义上也是为儿子聚拢人气。梅葆玖演出的剧目有《四郎探母》《玉堂春》《生死恨》和《木兰从军》。我小的时候听父亲说到梅葆玖先生时,对其扮相和演技评价一般,估计就是那次观摩时的印象。后来,再从电视上看了梅葆玖先生的戏,父亲说比过去好了太多。
父亲他们一行人,和梅兰芳先生碰巧住在一个旅馆。每天晚上看完戏回旅馆吃夜宵时,父亲他们一桌,梅先生他们一桌,彼此也会寒暄和简短地交谈。父亲说他那时太嫩生,没有和梅兰芳先生太多深入地交流。“嫩生”,在合肥话里的意思是腼腆、有些放不开。父亲那时候才25岁,“嫩生”一些可以理解,但25岁正是追星的年纪啊,搁现在,能够见到梅兰芳这样的大牌名角,可不是分分钟扑过去,合影、签名、搭讪吗?怎么可能只是含蓄矜持地点点头、笑笑,或者最多客套几句。时过境迁,果真是现在人理解不了过去的人,更何况父亲的骨子里,还有那说不清道不明的气息呢。那种气息里有傲气,还有其他一些东西,正是它们,让父亲嫩生、矜持而含蓄。
1977年后,父亲从农村回到城市,被分配到合肥市青年京剧团工作,先是编剧,后来当了剧团的负责人。
合肥市青年京剧团,可以说是以团代校的京剧新科班,建于1970年,起先叫“宣传队”。宣传队挑选幼童六十余名,习唱京剧。主要教师有曹畹秋、张福通、丁宝珊等,1975年正式以剧团命名。虽然剧团成立于非常时期,依然能够以科班形式,扎实地训练了小演员们四年基本功。1977年以后,又补授了京剧传统戏和戏曲特技内容,同时展开创作和演出活动,让学员在实践中提高。几年间,共创作、移植传统剧目达四十多台,有些剧目演出场次超过一百场。新创作剧目《红缨似火》,也连演七十余场,江苏、河南等十五个省、市、地区都曾派人前来观摩,并纷纷移植上演。此剧还曾赴多地巡回演出,省内外各媒体纷纷予以报道。合肥市政府曾以剧团的《孙悟空三打白骨精》,招待日本的访问代表团;以《郑成功·背父报国》,招待驻肥部队官兵;南京市政府,还曾以《红缨似火》,招待法国友人。
1982年8月,长大了同时技艺也日臻成熟的合肥青年京剧团的年轻演员们,参加了合肥市青年演员艺术汇报演出,获奖数名列第一。
汇演进行过程中,全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著名剧作家曹禺先生,恰好来到合肥。市有关部门邀请他观看市青年京剧团演出的一台折子戏。青年京剧团演出了传统京剧《罗成叫关》《花田错》《赤桑镇》《将相和》《李慧娘》等片段。演出结束后,曹禺和省市领导同志,登台接见了全体演员并合影留念。曹禺同志热情赞扬戏演得精彩,他说:“演出成功,前途无量,后继有人,京剧事业的未来靠你们。”当市文化局艺术科科长马宏业,向曹禺先生介绍我父亲“这是京剧团刘定九团长”时,曹禺很亲切地握着我父亲的手说:“感谢你培养这批好青年,培养这些好演员。”又说:“很好,很好,祝贺演出获得很大成功!”
前几天,我找出曹禺先生和我父亲握手的照片。妻子在一旁说,当时父亲尽管很精神,但显得有些憔悴,胡子似乎都没有刮。我说,你知道老人家那时候有多忙,又是多么的操心?
转眼近四十年过去了,剧团早已经解散,当年那些年轻的演员们也四处散去。他们最好的年华,最精彩的瞬间,定格在一张张黑白照片里,至今看来,依然能感受到那英气逼人的气息与魅力。
在92岁老父亲这儿,那些他见过、接触过的名流,和青年京剧团的那些年轻的演员,他始终都记着在。
时而,他会想起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