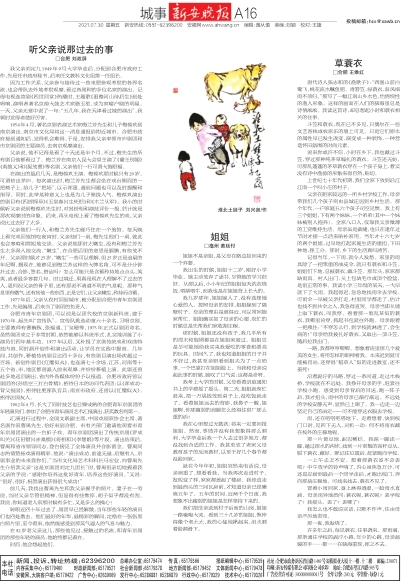发布日期:
草蓑衣
□合肥王维红
唐代诗人张志和的《渔歌子》:“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描写了一幅江南山乡水色,怡情悦性的渔人形象。这样的画面在人们的脑海里总是诗情浓浓。我读这首诗,却总想起小时和蓑衣相关的往事。
斗笠和蓑衣,现在已不多见,只偶尔在一些文艺客栈或农家乐的墙上可见。只是它们原本的属性早已发生改变,演变成一种装饰,一种营造怀旧氛围的时尚元素。
说来你或许不信,小时在乡下,我也戴过斗笠,穿过那种纯茅草编扎的蓑衣。斗笠还无妨,可那乱蓬蓬的茅草蓑衣穿在一个孩子身上,着实没有诗中渔翁的形象来得自然、贴切。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我们全家下放到沿江江南一个叫小庄的村子。
父亲在距家较远的一所乡村学校工作,母亲带我们几个孩子则由县城迁居到乡村生活。那个年代,一户家庭五六个孩子司空见惯。我上有三个姐姐,下有两个妹妹、一个弟弟(其中一个妹妹被别人抱养)。全家八口人,仅靠我父亲微薄的工资维持生活。母亲虽是裁缝,也只在逢年过节时才接一点活来贴补家用。当年才十六七岁的两个姐姐,过早地扛起家庭生活的重担,下田种地,挣工分。那时,乡下的生活真叫清苦。
记得当年,一下雨,就令人发愁。家里的雨具除了一把笨重的油皮伞,就只有蓑衣和斗笠。姐姐们下地,总披蓑衣,戴斗笠。那年头,家家都缺雨具。村人出门,头上包块毛巾或顶个脸盆,是很正常的事。我读小学三年级的某天,一大早就下了大雨。我起得迟,急急地找雨伞去学校。可雨伞一早被父亲打走,村里同学都走了,估计也找不到共伞之人,我急得直哭。母亲当即从墙上取下蓑衣,叫我穿。看着那一堆乱草似的蓑衣,我哪里肯穿,抓起书包就往外跑。母亲跟着一把拽住:“不穿怎么行,到学校就淋透了,会生病的!”母亲给我披扎好蓑衣,又取出一顶斗笠,随后拉我出门。
一路,我都哼哼唧唧。想象着班里那几个爱美的女生,将用怎样的眼神看我。本来迟到就可能被罚站,还穿得“稻草人”似的走进教室,还不羞死?
沿着泥泞的马路,穿过一条河道,走过木栈桥,学校就在不远处。我挣开母亲的手,赶紧往学校小跑。感受到母亲背后的目送,跑一阵子后,我才扭头,雨中的母亲已渐行渐远。不远处的学校安静无声,显然已上课了。我一边走一边坚定自己的决定——可不能穿这衣服去学校。
雨,还在吧嗒吧嗒地下。走着想着,快到校门口时,见四下无人,灵机一动:何不将雨衣藏在校外的庄稼地呢。
那一片黄豆地,泥巴稀烂。我深一脚浅一脚,趟过浑水的沟坎,找到一片密集的高秆豆丛,脱下蓑衣,藏好。默记住位置后,赶紧跑向学校。
一上午忐忑不安。想着那蓑衣该不会丢吧?中午放学的铃声响了,内心虽焦急万分,可还是忍耐到最后一个同学走后,才跑出校门,奔向那块庄稼地。可找来找去,蓑衣不见了。
冒着小雨回家,身上淋得透湿,一脸雨水直淌。母亲诧异地质问:蓑衣呢,蓑衣呢?丢学校了?我摇头。丢了?丢哪了?
我怎么也不敢说实话,只默不作声,任由母亲严厉地责骂。
那一夜,我发烧了。
许多年之后,每见蓑衣,往事袭来。那雨滴,那条通往学校的泥泞小路,年少的心跳,母亲温暖的手……都一一在脑海重现,挥之不去。
唐代诗人张志和的《渔歌子》:“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描写了一幅江南山乡水色,怡情悦性的渔人形象。这样的画面在人们的脑海里总是诗情浓浓。我读这首诗,却总想起小时和蓑衣相关的往事。
斗笠和蓑衣,现在已不多见,只偶尔在一些文艺客栈或农家乐的墙上可见。只是它们原本的属性早已发生改变,演变成一种装饰,一种营造怀旧氛围的时尚元素。
说来你或许不信,小时在乡下,我也戴过斗笠,穿过那种纯茅草编扎的蓑衣。斗笠还无妨,可那乱蓬蓬的茅草蓑衣穿在一个孩子身上,着实没有诗中渔翁的形象来得自然、贴切。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我们全家下放到沿江江南一个叫小庄的村子。
父亲在距家较远的一所乡村学校工作,母亲带我们几个孩子则由县城迁居到乡村生活。那个年代,一户家庭五六个孩子司空见惯。我上有三个姐姐,下有两个妹妹、一个弟弟(其中一个妹妹被别人抱养)。全家八口人,仅靠我父亲微薄的工资维持生活。母亲虽是裁缝,也只在逢年过节时才接一点活来贴补家用。当年才十六七岁的两个姐姐,过早地扛起家庭生活的重担,下田种地,挣工分。那时,乡下的生活真叫清苦。
记得当年,一下雨,就令人发愁。家里的雨具除了一把笨重的油皮伞,就只有蓑衣和斗笠。姐姐们下地,总披蓑衣,戴斗笠。那年头,家家都缺雨具。村人出门,头上包块毛巾或顶个脸盆,是很正常的事。我读小学三年级的某天,一大早就下了大雨。我起得迟,急急地找雨伞去学校。可雨伞一早被父亲打走,村里同学都走了,估计也找不到共伞之人,我急得直哭。母亲当即从墙上取下蓑衣,叫我穿。看着那一堆乱草似的蓑衣,我哪里肯穿,抓起书包就往外跑。母亲跟着一把拽住:“不穿怎么行,到学校就淋透了,会生病的!”母亲给我披扎好蓑衣,又取出一顶斗笠,随后拉我出门。
一路,我都哼哼唧唧。想象着班里那几个爱美的女生,将用怎样的眼神看我。本来迟到就可能被罚站,还穿得“稻草人”似的走进教室,还不羞死?
沿着泥泞的马路,穿过一条河道,走过木栈桥,学校就在不远处。我挣开母亲的手,赶紧往学校小跑。感受到母亲背后的目送,跑一阵子后,我才扭头,雨中的母亲已渐行渐远。不远处的学校安静无声,显然已上课了。我一边走一边坚定自己的决定——可不能穿这衣服去学校。
雨,还在吧嗒吧嗒地下。走着想着,快到校门口时,见四下无人,灵机一动:何不将雨衣藏在校外的庄稼地呢。
那一片黄豆地,泥巴稀烂。我深一脚浅一脚,趟过浑水的沟坎,找到一片密集的高秆豆丛,脱下蓑衣,藏好。默记住位置后,赶紧跑向学校。
一上午忐忑不安。想着那蓑衣该不会丢吧?中午放学的铃声响了,内心虽焦急万分,可还是忍耐到最后一个同学走后,才跑出校门,奔向那块庄稼地。可找来找去,蓑衣不见了。
冒着小雨回家,身上淋得透湿,一脸雨水直淌。母亲诧异地质问:蓑衣呢,蓑衣呢?丢学校了?我摇头。丢了?丢哪了?
我怎么也不敢说实话,只默不作声,任由母亲严厉地责骂。
那一夜,我发烧了。
许多年之后,每见蓑衣,往事袭来。那雨滴,那条通往学校的泥泞小路,年少的心跳,母亲温暖的手……都一一在脑海重现,挥之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