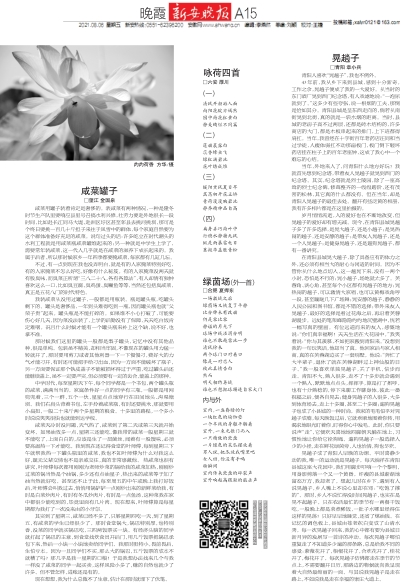发布日期:
咸菜罐子
□望江金国泉
咸菜用罐子装着肯定是奢侈的。装咸菜有两种情况,一种是隆冬时节生产队里要响应县里号召搞水利兴修,壮劳力要赴外地很长一段时间,比如赴长江同马大堤、赴洲区圩区甚至邻县去挑河挑坝,那可是个终日要挑一百几十斤担子来往于风雪中的群体,每个家庭自然要为这个群体准备好充足的咸菜。说句过头的话:许多屹立在时代潮头的水利工程就是用咸菜瓶咸菜罐堆起来的;另一种就是中学生上学了,需要常年装咸菜,这一代人几乎就是在咸菜的滋养下成长起来的。我属于后者,所以那时候家乡一年四季都要腌咸菜,每家都有几缸几坛。
不过,有一点到现在我也没弄明白,就是有的人家腌菜特别好吃,有的人家腌菜不怎么好吃,好像有什么秘笈。有的人家腌菜没两天就有股臭味,而臭菜正所谓“三八二十八,各有各算法”,有人却情有独钟喜欢这么一口,比如臭豆腐、臭鸡蛋、臭鳜鱼等等,当然还包括臭咸菜,真正是五花八门的时代特色。
我装咸菜从没用过罐子,一般都是用瓶装。瓶是罐头瓶,吃罐头剩下的。罐头是奢侈品,一年到头难得吃到一瓶,因而罐头瓶也就“父荣子贵”起来。罐头瓶是不能打碎的。如果谁不小心打破了,可能要伤心好几天,因为菜没法装了,上学的后勤没有了保障,天天吃白饭肯定难咽。况且什么时候才能有一个罐头瓶来补上这个缺,说不好,也拿不准。
那时候我们这里的罐头一般都是梨子罐头,记忆中没有其他品种,很是单纯。包装虽不精美,却相当牢固,不像现在的罐头用力猛一转就开了,那时要用剪刀或者其他利器一下一下慢慢刁,费好大的力气才能刁开,有时还可能把手给刁出血,因为一方面不能破坏了瓶子,另一方面要保证那个铁皮盖子不能被损坏得过于严重,吃过罐头后还能继续盖上,虽不一定要严实,但必须要有一定的齿合,能盖上的那种。
中学时代,每至星期天下午,每个同学都是一个书包,两个罐头瓶的咸菜,满满当当的。家庭条件好一点的同学有三瓶,一般都是用网兜兜着,三个一群,五个一伙,星星点点地穿行在田间地头、沟渠塘坝。我们右肩头背着书包,左手拎着咸菜瓶,有时还要挑米,那就要用小扁担,一般二十来斤两个多星期的粮食。十多里的路程,一个多小时说说笑笑很快也就能到达学校。
咸菜天冷时没问题,天气热了,咸菜到了第二天或第三天就开始变坏。如果油放多一点,星期三还能吃,像我带的咸菜一般星期三就不能吃了,上面白白的,应该是生了一层菌丝,闻着有一股馊味,必须要高温热一下才能吃。我到现在还记得食堂的叶师傅,每到星期三下午就帮我热一下罐头瓶里的咸菜,我也不知叶师傅为什么对我这么好,既无父辈交情也不是亲戚交往,真的非常感激他。热咸菜也很有讲究,叶师傅每次都用刚刚为老师炒菜的锅给我的咸菜加热,刚刚炒过菜的锅当然是个油锅,多少还有点油星子,热出来的咸菜等于加了油当然就好吃。甚至还不止于此,每至周五的中午或晚上我打好饭后,叶师傅会叫我过去,悄悄用锅铲铲一点刚炒出来的新鲜菜给我,有时是白菜炒肉片,有时有冬瓜炒肉片,有时是一点鱼汤,这种菜我在家中都很少能吃到的,毕竟里面有几片肉。现在想来,叶师傅算是每星期都为我打了一次没来由的小牙祭。
其实到了星期三,咸菜已经不多了,只够星期四吃一天,到了星期五,有咸菜的学生已经很少了。那时食堂锅大,锅巴特别厚,也特别香,没菜的同学就买锅巴吃,三四两饭票买一块。有经济头脑的同学就打起了锅巴的主意,到食堂找炊食员开后门,用几斤饭票把锅巴承包下来,然后一小块一小块地卖给同学们。我那时胆特小,畏前畏后,生怕亏本。因为一旦同学们不买,那么大的锅巴,五斤饭票的成本不就糟了吗?那几乎是我一星期的口粮!于是我想办法找来几个与我一样没了咸菜的同学一起买卖,这样风险小多了,赚的自然也就少了许多。但不管怎样,进账还是有的。
现在想想,我为什么总做不了生意,估计在那时就埋下了伏笔。
咸菜用罐子装着肯定是奢侈的。装咸菜有两种情况,一种是隆冬时节生产队里要响应县里号召搞水利兴修,壮劳力要赴外地很长一段时间,比如赴长江同马大堤、赴洲区圩区甚至邻县去挑河挑坝,那可是个终日要挑一百几十斤担子来往于风雪中的群体,每个家庭自然要为这个群体准备好充足的咸菜。说句过头的话:许多屹立在时代潮头的水利工程就是用咸菜瓶咸菜罐堆起来的;另一种就是中学生上学了,需要常年装咸菜,这一代人几乎就是在咸菜的滋养下成长起来的。我属于后者,所以那时候家乡一年四季都要腌咸菜,每家都有几缸几坛。
不过,有一点到现在我也没弄明白,就是有的人家腌菜特别好吃,有的人家腌菜不怎么好吃,好像有什么秘笈。有的人家腌菜没两天就有股臭味,而臭菜正所谓“三八二十八,各有各算法”,有人却情有独钟喜欢这么一口,比如臭豆腐、臭鸡蛋、臭鳜鱼等等,当然还包括臭咸菜,真正是五花八门的时代特色。
我装咸菜从没用过罐子,一般都是用瓶装。瓶是罐头瓶,吃罐头剩下的。罐头是奢侈品,一年到头难得吃到一瓶,因而罐头瓶也就“父荣子贵”起来。罐头瓶是不能打碎的。如果谁不小心打破了,可能要伤心好几天,因为菜没法装了,上学的后勤没有了保障,天天吃白饭肯定难咽。况且什么时候才能有一个罐头瓶来补上这个缺,说不好,也拿不准。
那时候我们这里的罐头一般都是梨子罐头,记忆中没有其他品种,很是单纯。包装虽不精美,却相当牢固,不像现在的罐头用力猛一转就开了,那时要用剪刀或者其他利器一下一下慢慢刁,费好大的力气才能刁开,有时还可能把手给刁出血,因为一方面不能破坏了瓶子,另一方面要保证那个铁皮盖子不能被损坏得过于严重,吃过罐头后还能继续盖上,虽不一定要严实,但必须要有一定的齿合,能盖上的那种。
中学时代,每至星期天下午,每个同学都是一个书包,两个罐头瓶的咸菜,满满当当的。家庭条件好一点的同学有三瓶,一般都是用网兜兜着,三个一群,五个一伙,星星点点地穿行在田间地头、沟渠塘坝。我们右肩头背着书包,左手拎着咸菜瓶,有时还要挑米,那就要用小扁担,一般二十来斤两个多星期的粮食。十多里的路程,一个多小时说说笑笑很快也就能到达学校。
咸菜天冷时没问题,天气热了,咸菜到了第二天或第三天就开始变坏。如果油放多一点,星期三还能吃,像我带的咸菜一般星期三就不能吃了,上面白白的,应该是生了一层菌丝,闻着有一股馊味,必须要高温热一下才能吃。我到现在还记得食堂的叶师傅,每到星期三下午就帮我热一下罐头瓶里的咸菜,我也不知叶师傅为什么对我这么好,既无父辈交情也不是亲戚交往,真的非常感激他。热咸菜也很有讲究,叶师傅每次都用刚刚为老师炒菜的锅给我的咸菜加热,刚刚炒过菜的锅当然是个油锅,多少还有点油星子,热出来的咸菜等于加了油当然就好吃。甚至还不止于此,每至周五的中午或晚上我打好饭后,叶师傅会叫我过去,悄悄用锅铲铲一点刚炒出来的新鲜菜给我,有时是白菜炒肉片,有时有冬瓜炒肉片,有时是一点鱼汤,这种菜我在家中都很少能吃到的,毕竟里面有几片肉。现在想来,叶师傅算是每星期都为我打了一次没来由的小牙祭。
其实到了星期三,咸菜已经不多了,只够星期四吃一天,到了星期五,有咸菜的学生已经很少了。那时食堂锅大,锅巴特别厚,也特别香,没菜的同学就买锅巴吃,三四两饭票买一块。有经济头脑的同学就打起了锅巴的主意,到食堂找炊食员开后门,用几斤饭票把锅巴承包下来,然后一小块一小块地卖给同学们。我那时胆特小,畏前畏后,生怕亏本。因为一旦同学们不买,那么大的锅巴,五斤饭票的成本不就糟了吗?那几乎是我一星期的口粮!于是我想办法找来几个与我一样没了咸菜的同学一起买卖,这样风险小多了,赚的自然也就少了许多。但不管怎样,进账还是有的。
现在想想,我为什么总做不了生意,估计在那时就埋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