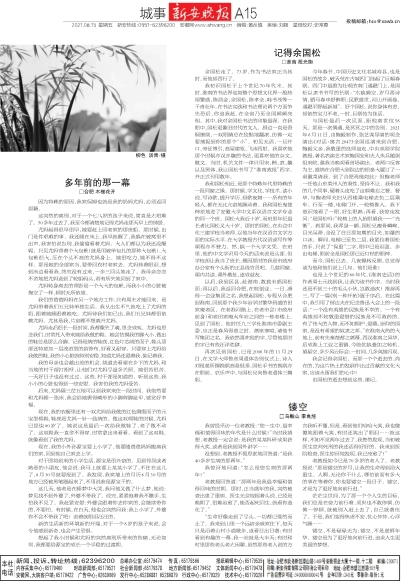发布日期:
记得余国松
□淮南殷光衡
余国松走了。73岁,作为书法家正当其时,而他却西行了。
我初识国松于上个世纪70年代末。其时,淮南的书法界也如整个思想文化界一般热闹繁盛,陈浩金、余国松、陈孝全、韩书茂等一干青壮年,在书法实践和书法理论两个方面争先恐后,你追我赶,在全省乃至全国频频亮相。其中,我对余国松书法的印象最深。在我眼中,国松更像旧时代的文人。唇边一直是香烟缭绕,一双眼睛总在狡黠地翻滚,仿佛一定要捕捉到你的那个“小”。初见无语,一旦开口,旁征博引,高屋建瓴,飞沫四射。我喜欢他那个时候亦汉亦魏的书法,更喜欢他的杂文、散文。当时,机关文件一律只用宋、楷、隶、魏以及黑体,我让国松书写了“淮南政报”四字,并正式刊用数年。
我和国松相近,是那个特殊年代里特殊的一段同窗之缘。那时候,学文化,学技术,读小说,写诗歌,提升学历,昼歌夜舞……所有的年轻人,都在无比亢奋地躁动着。我和国松鬼使神差地进了安徽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同一个班。国松大我近十岁,而班里年纪最长者比国松又大十岁。那时的国松,在央企中化三建学校当老师,以他当年在汉语言文学方面的实际水平,在大学教授古代汉语或写作等课程亦不费力。然,缺一个大学文凭。在班里,他的中文学识用今天的话来说是头部,但学校却让我当了班长,概因那时的我是市政府办公室有个头衔的正县级官员吧。几载同窗,课内共读,课外散扯,遂成益友。
以后,我到区县、赴海南,数载未晤国松面;再以后,我返回合肥,在皖创业。一日,凑得一企业集团之名,我想起国松,专程从合肥到淮南,回到那个我少年治学时繁华昌盛的田家庵老区。在老淮河路上,在老市会(市政府前身)和老田家庵火车站之间的一栋老楼上,见到了国松。他时任九三学社淮南市委副主委,应正是春风得意之时。落座寒暄,请他书写集团之名。我依然喜欢他的字,尽管他那时的字已有些汪洋恣肆。
再次见到国松,已是2006年的11月29日,在文学大师鲁彦周遗体告别仪式上,诗人刘祖慈所撰挽联高悬低垂,国松手书的挽联亦在眼前。哀乐声中,与国松兄向鲁老遗体三鞠躬。
今年春节,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寿县,也是国松的故乡,破天荒在古城四门挂起了巨幅春联。四门中最蔚为壮观的南门通淝门上,是国松以隶书书写的长联:“水映晴空,岁月荡诗情,驷马春申舒醉眼;民歌盛世,河山开画卷,通淝平野起新城”。好个国松,说你身体有恙,却依然宝刀不老,一时,巨联传为佳话。
与国松最后一次见面,距他离世仅56天。那是一次偶遇,是冥冥之中的告别。2021年6月11日,由鲍毅制作、张艺谋导演的观念演出《对话·寓言2047》全国巡演来到合肥。鲍毅父亲,我敬重的良师益友、中央戏剧学院教授、著名表演艺术家鲍国安和夫人朱兵随剧组来皖,邀我当晚观看首场演出。老两口反客为主,盛情在合肥大剧院边的银泰大厦订了一桌徽菜请我。到了合肥焉能如此?但鲍老师一任他山东莱州人的秉性,坚持不让。我和我的几个同事,硬着头皮吃了这顿难忘之餐。餐毕,与鲍老师夫妇从四楼乘电梯去负二层乘车。行至一楼,电梯门开,一轮椅推入。我下意识地看了一眼,好生眼熟;再看,我惊诧发问:“是国松吗?”轮椅上的人抬眼望我——“光衡”。刹那间,我浑身一颤,国松兄瘦骨嶙峋,目光呆滞,全没了往日那如鹰的目光,如瀑的口沫。瞬间,电梯已至负二层,我紧拉着国松的手,只说了“保重”二字,眼中已是泪盈。步出电梯,眼前全是国松那已近灯枯的眼神。
而今,国松已去。几夜辗转反侧,总觉得该为他和他们说上几句。他们是谁?
也是上个世纪的80年代,《淮南史话》的作者周士元找到我,让我为该书作序。当时我还是不到三十的毛头小伙,岂敢造次!推辞再三,写了一篇《别一种开拓》置于序后。在此篇中,我引用了郁达夫在纪念鲁迅大会上的一段话:“一个没有英雄的民族是不幸的。一个有英雄却不知敬重爱惜的民族是不可救药的。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在淮南火热的大地上,前有先秦楚都之落幕,西汉淮南之风华,后成淮上工业之重镇,今临优缺叠加之转机。望星空,多少风云际会;一时间,几多英雄闪现。
我会记得余国松。而那一个个逝去的、尚在的,为这片热土的发展作出过贡献的文化大家,应该永留我们的心中!
由国松的逝去想到这些,谨记。
余国松走了。73岁,作为书法家正当其时,而他却西行了。
我初识国松于上个世纪70年代末。其时,淮南的书法界也如整个思想文化界一般热闹繁盛,陈浩金、余国松、陈孝全、韩书茂等一干青壮年,在书法实践和书法理论两个方面争先恐后,你追我赶,在全省乃至全国频频亮相。其中,我对余国松书法的印象最深。在我眼中,国松更像旧时代的文人。唇边一直是香烟缭绕,一双眼睛总在狡黠地翻滚,仿佛一定要捕捉到你的那个“小”。初见无语,一旦开口,旁征博引,高屋建瓴,飞沫四射。我喜欢他那个时候亦汉亦魏的书法,更喜欢他的杂文、散文。当时,机关文件一律只用宋、楷、隶、魏以及黑体,我让国松书写了“淮南政报”四字,并正式刊用数年。
我和国松相近,是那个特殊年代里特殊的一段同窗之缘。那时候,学文化,学技术,读小说,写诗歌,提升学历,昼歌夜舞……所有的年轻人,都在无比亢奋地躁动着。我和国松鬼使神差地进了安徽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同一个班。国松大我近十岁,而班里年纪最长者比国松又大十岁。那时的国松,在央企中化三建学校当老师,以他当年在汉语言文学方面的实际水平,在大学教授古代汉语或写作等课程亦不费力。然,缺一个大学文凭。在班里,他的中文学识用今天的话来说是头部,但学校却让我当了班长,概因那时的我是市政府办公室有个头衔的正县级官员吧。几载同窗,课内共读,课外散扯,遂成益友。
以后,我到区县、赴海南,数载未晤国松面;再以后,我返回合肥,在皖创业。一日,凑得一企业集团之名,我想起国松,专程从合肥到淮南,回到那个我少年治学时繁华昌盛的田家庵老区。在老淮河路上,在老市会(市政府前身)和老田家庵火车站之间的一栋老楼上,见到了国松。他时任九三学社淮南市委副主委,应正是春风得意之时。落座寒暄,请他书写集团之名。我依然喜欢他的字,尽管他那时的字已有些汪洋恣肆。
再次见到国松,已是2006年的11月29日,在文学大师鲁彦周遗体告别仪式上,诗人刘祖慈所撰挽联高悬低垂,国松手书的挽联亦在眼前。哀乐声中,与国松兄向鲁老遗体三鞠躬。
今年春节,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寿县,也是国松的故乡,破天荒在古城四门挂起了巨幅春联。四门中最蔚为壮观的南门通淝门上,是国松以隶书书写的长联:“水映晴空,岁月荡诗情,驷马春申舒醉眼;民歌盛世,河山开画卷,通淝平野起新城”。好个国松,说你身体有恙,却依然宝刀不老,一时,巨联传为佳话。
与国松最后一次见面,距他离世仅56天。那是一次偶遇,是冥冥之中的告别。2021年6月11日,由鲍毅制作、张艺谋导演的观念演出《对话·寓言2047》全国巡演来到合肥。鲍毅父亲,我敬重的良师益友、中央戏剧学院教授、著名表演艺术家鲍国安和夫人朱兵随剧组来皖,邀我当晚观看首场演出。老两口反客为主,盛情在合肥大剧院边的银泰大厦订了一桌徽菜请我。到了合肥焉能如此?但鲍老师一任他山东莱州人的秉性,坚持不让。我和我的几个同事,硬着头皮吃了这顿难忘之餐。餐毕,与鲍老师夫妇从四楼乘电梯去负二层乘车。行至一楼,电梯门开,一轮椅推入。我下意识地看了一眼,好生眼熟;再看,我惊诧发问:“是国松吗?”轮椅上的人抬眼望我——“光衡”。刹那间,我浑身一颤,国松兄瘦骨嶙峋,目光呆滞,全没了往日那如鹰的目光,如瀑的口沫。瞬间,电梯已至负二层,我紧拉着国松的手,只说了“保重”二字,眼中已是泪盈。步出电梯,眼前全是国松那已近灯枯的眼神。
而今,国松已去。几夜辗转反侧,总觉得该为他和他们说上几句。他们是谁?
也是上个世纪的80年代,《淮南史话》的作者周士元找到我,让我为该书作序。当时我还是不到三十的毛头小伙,岂敢造次!推辞再三,写了一篇《别一种开拓》置于序后。在此篇中,我引用了郁达夫在纪念鲁迅大会上的一段话:“一个没有英雄的民族是不幸的。一个有英雄却不知敬重爱惜的民族是不可救药的。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在淮南火热的大地上,前有先秦楚都之落幕,西汉淮南之风华,后成淮上工业之重镇,今临优缺叠加之转机。望星空,多少风云际会;一时间,几多英雄闪现。
我会记得余国松。而那一个个逝去的、尚在的,为这片热土的发展作出过贡献的文化大家,应该永留我们的心中!
由国松的逝去想到这些,谨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