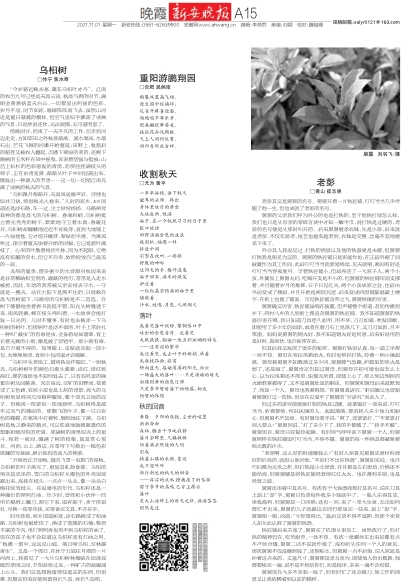发布日期:
老彭
□黄山崔志强
老彭其实是舅舅的名号。舅舅开着一爿铁匠铺,叮叮当当几乎伴随了他一生,但也成就了老彭的名号。
舅舅的父亲我们呼为外公的也是打铁的,至于他铁打得怎么样,我们也只是从母亲的零碎言谈中才知一鳞半爪,说打铁是过硬的,老彭的名号便是从那时叫开的。后来舅舅继承衣钵,先是小彭,后来就是老彭,不仅年龄老,技艺也越来越老到,衣钵是完整、丝毫不差地继承下来了。
外公其人我没见过,打铁的情景以及他的铁器更是未睹,但舅舅打铁我是眼见为实的。舅舅的铁匠铺只是家庭作坊,在正房外砌了间披厦作为其工作间,此后叮叮当当就萦屋绕梁,见天就响,晚间有时还叮叮当当穿夜度月。尽管铁匠铺小,但却养活了一大家子人,两个小孩、外婆加上舅舅夫妇,吃喝开支是不小的,但舅舅的铁匠铺牢固支撑着,并且随着岁月的推移,日子日见红火,两个小孩成家立业,住房由平房变成了楼房,并且开始是两层瓦屋,后来变成四层钢筋混凝土楼宇,在街上也置了铺面。可见铁匠铺功劳之大,舅舅铁锤的厉害。
舅舅确实厉害,铁匠铺虽响在披厦,但声铺整个街道,甚而传播到乡下,四村八乡的人到街上都直奔舅舅的铁匠铺。我不知道舅舅的铁器厉害在哪,我只知道刀具经久耐用,用不坏,刀刃如霜,吹发即断。即使用了多少年仍如斯,或者在磨刀石上晃荡几下,又刀刃如新,且不笨重。妈妈说舅舅的钢火好,我不知道钢火好是何意,后来听说用的是好料,真家伙,也许秘密在此。
但其后我又发现了更多的秘密。舅舅打铁很认真,每一道工序都一丝不苟。舅母在旁拉风箱添火,有时也帮衬打铁,拎着一柄小锤起落。舅母被舅舅不知数落过多少回,舅舅脾气急躁,炉膛里的炭火是弱了,还是强了,舅舅肯定告知过舅母,但舅母开初可能也没怎么上心,以为拉风箱还不简单,快慢无所谓,即使上心了,那么到边倒拐的火候谁掌握得了,又不是舅舅肚里的蛔虫。但舅舅和舅母后来就默契了,宛如一个人。舅母也笑着抱怨:“你舅舅真讲究。”听说姨父也曾跟着舅舅打过一阵铁,但实在忍受不了舅舅的“穷讲究”而走人了。
但过多的讲究使舅舅打制的铁具过硬。就拿锻打一项来说,叮叮当当,听着都烦,何况执锤的人。起起落落,要消耗人多少体力和耐心,但舅舅不厌其烦。有时舅母罢手说:“照了,还紧紧打。”“不紧紧打别人要么?”舅舅回说。“打了多少下了,我的手都酸了。”“我手不酸”,舅舅坦言,舅母只好复拎起锤。有时则气呼呼丢下舅舅一个人,但舅舅照样在铁匠铺里叮叮当当,不停不辍。舅舅的每一件铁具都凝聚着他无数的汗水。
“老彭啊,这么好的料能赚钱么?”有时人家看见舅舅买原材料择好的价高的,就担心地问他。“不好打不出好铁器”,舅舅如实说。也许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但打铁是小本经营,并且都是左右街坊,价格还不能给高,但舅舅硬是将铁匠铺经营得红红火火。也许薄利多销,也是经营之道。
舅舅还很看中其名号。有次有个大铁器商想打其名号,说在刀具上刻上“彭”字,舅舅只负责每件收多少钱就中了。一般人乐得其成,坐收渔利,但舅舅却一口回绝;还有一回,来了一单大生意,无论如何都忙不出来,舅舅的儿子就提议在同行那里买一些来,刻上“彭”字。舅舅眼一瞪,凶道:“亏你想得出。”最后交货不得不延期,但那个卖货人却从此认准了舅舅的铁器。
铁匠铺后来关张了,舅舅买了机器从事加工。虽然改行了,但打铁的精神仍在,吃苦耐劳,一丝不苟。有次一批螺丝车出来好像有点不严丝合缝,舅舅二话不说就作废了,没有听从任何一个人的意见。那次舅舅不仅没赚到钱了,还倒贴本,但舅舅一点不后悔,说人家就是冲着这点来的。丈量尺寸,舅舅都是亲力亲为,即使他人给出数据,他都要核实一遍,说不是不相信你们,而是程序,多来一遍不会有错。
舅舅现在大多不亲临一线了,但有时忙了还会操刀,他工作的情景又让我依稀看到以前的模样。
老彭其实是舅舅的名号。舅舅开着一爿铁匠铺,叮叮当当几乎伴随了他一生,但也成就了老彭的名号。
舅舅的父亲我们呼为外公的也是打铁的,至于他铁打得怎么样,我们也只是从母亲的零碎言谈中才知一鳞半爪,说打铁是过硬的,老彭的名号便是从那时叫开的。后来舅舅继承衣钵,先是小彭,后来就是老彭,不仅年龄老,技艺也越来越老到,衣钵是完整、丝毫不差地继承下来了。
外公其人我没见过,打铁的情景以及他的铁器更是未睹,但舅舅打铁我是眼见为实的。舅舅的铁匠铺只是家庭作坊,在正房外砌了间披厦作为其工作间,此后叮叮当当就萦屋绕梁,见天就响,晚间有时还叮叮当当穿夜度月。尽管铁匠铺小,但却养活了一大家子人,两个小孩、外婆加上舅舅夫妇,吃喝开支是不小的,但舅舅的铁匠铺牢固支撑着,并且随着岁月的推移,日子日见红火,两个小孩成家立业,住房由平房变成了楼房,并且开始是两层瓦屋,后来变成四层钢筋混凝土楼宇,在街上也置了铺面。可见铁匠铺功劳之大,舅舅铁锤的厉害。
舅舅确实厉害,铁匠铺虽响在披厦,但声铺整个街道,甚而传播到乡下,四村八乡的人到街上都直奔舅舅的铁匠铺。我不知道舅舅的铁器厉害在哪,我只知道刀具经久耐用,用不坏,刀刃如霜,吹发即断。即使用了多少年仍如斯,或者在磨刀石上晃荡几下,又刀刃如新,且不笨重。妈妈说舅舅的钢火好,我不知道钢火好是何意,后来听说用的是好料,真家伙,也许秘密在此。
但其后我又发现了更多的秘密。舅舅打铁很认真,每一道工序都一丝不苟。舅母在旁拉风箱添火,有时也帮衬打铁,拎着一柄小锤起落。舅母被舅舅不知数落过多少回,舅舅脾气急躁,炉膛里的炭火是弱了,还是强了,舅舅肯定告知过舅母,但舅母开初可能也没怎么上心,以为拉风箱还不简单,快慢无所谓,即使上心了,那么到边倒拐的火候谁掌握得了,又不是舅舅肚里的蛔虫。但舅舅和舅母后来就默契了,宛如一个人。舅母也笑着抱怨:“你舅舅真讲究。”听说姨父也曾跟着舅舅打过一阵铁,但实在忍受不了舅舅的“穷讲究”而走人了。
但过多的讲究使舅舅打制的铁具过硬。就拿锻打一项来说,叮叮当当,听着都烦,何况执锤的人。起起落落,要消耗人多少体力和耐心,但舅舅不厌其烦。有时舅母罢手说:“照了,还紧紧打。”“不紧紧打别人要么?”舅舅回说。“打了多少下了,我的手都酸了。”“我手不酸”,舅舅坦言,舅母只好复拎起锤。有时则气呼呼丢下舅舅一个人,但舅舅照样在铁匠铺里叮叮当当,不停不辍。舅舅的每一件铁具都凝聚着他无数的汗水。
“老彭啊,这么好的料能赚钱么?”有时人家看见舅舅买原材料择好的价高的,就担心地问他。“不好打不出好铁器”,舅舅如实说。也许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但打铁是小本经营,并且都是左右街坊,价格还不能给高,但舅舅硬是将铁匠铺经营得红红火火。也许薄利多销,也是经营之道。
舅舅还很看中其名号。有次有个大铁器商想打其名号,说在刀具上刻上“彭”字,舅舅只负责每件收多少钱就中了。一般人乐得其成,坐收渔利,但舅舅却一口回绝;还有一回,来了一单大生意,无论如何都忙不出来,舅舅的儿子就提议在同行那里买一些来,刻上“彭”字。舅舅眼一瞪,凶道:“亏你想得出。”最后交货不得不延期,但那个卖货人却从此认准了舅舅的铁器。
铁匠铺后来关张了,舅舅买了机器从事加工。虽然改行了,但打铁的精神仍在,吃苦耐劳,一丝不苟。有次一批螺丝车出来好像有点不严丝合缝,舅舅二话不说就作废了,没有听从任何一个人的意见。那次舅舅不仅没赚到钱了,还倒贴本,但舅舅一点不后悔,说人家就是冲着这点来的。丈量尺寸,舅舅都是亲力亲为,即使他人给出数据,他都要核实一遍,说不是不相信你们,而是程序,多来一遍不会有错。
舅舅现在大多不亲临一线了,但有时忙了还会操刀,他工作的情景又让我依稀看到以前的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