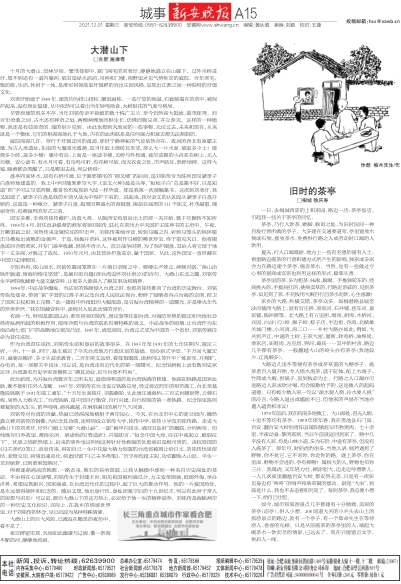发布日期:
大潜山下
□合肥施维奇
十月的大潜山,层林尽染。繁茂苍郁中,豪门深宅的刘老圩,静静地矗立在山脚下。过外吊桥进圩,想不到还有一道内壕沟,依旧是绿水滔滔、吊桥和门楼,视野里才见气势恢宏的庭院。百年老宅,集防御、生活、休闲于一体,是淮军将领故里圩堡群的突出庄园风格,呈现出江淮之间一种独特的圩堡文化。
刘老圩始建于1868年,建筑均为排山排柱,雕梁画栋。一些厅堂的地基、石础倾塌在荒草中,被保护起来,没有原址复建,从中依然可以看出当年钟鸣鼎食、火树银花的气度与格局。
尽管原建筑现多不存,当年刘铭传亲手栽植的数十株广玉兰,至今仍然高大挺拔,蓊茂郁秀。而百年沧桑之间,古木还有神奇之处,两棵两棵地同根生长,仿佛同胞兄弟,并立参天。这样的一种植物,我还是有些惊奇的,端的很少见到。由此也想到天地间的一些事物,无论过去、未来和现在,从来就是一个整体,它们的根深深地扎于大地,内在的血肉联系是任何强力和意志都无法割裂的。
庭院深深几许。穿行于圩堡迂回的甬道,那份宁静神秘的气息依然存在。故居的西北有座霸王墩,为古人类遗址;东南的大堰波光潋滟,是当年取土烧砖瓦形成,那么大一片水面,能取多少土?能烧多少砖、盖多少楼?堰中有岛,上面是一座读书楼,无桥与外相通,彼岸送餐的小舟系在树上,无人自横。安心读书,有水月可看,有鸟鸣可听,有花树可依,而无衣食之忧、市声聒耳、琐碎烦神。这样大福,睡着都会笑醒了,只是哪里去找,何以修得?
盘亭四面环水,却有石桥可通,位于驱邪镇宅的“钢叉楼”的后面,是刘铭传专为陈列国宝虢季子白盘特地建造的。我上中学时随族爹写大字,《金文六种》最是头疼,“桓桓子白”总是篆不好,只是知道“四”字可以写成四横,像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一样欣喜。那是我第一次接触篆书。这次到刘老圩,我又知道了,虢季子白盘是我的乡贤从战火中保护下来的。说起来,我对金文的认知是从虢季子白盘开始的,这真是一种缘分。虢季子白盘,殷周时期盛水的青铜器,铸刻在底部的111个铭文,朴茂凝重,瑰丽奇伟,有着强烈的形式之美。
国宝多难,幸得刘铭传藏护,功莫大焉。从陕西宝鸡眉县出土的那一天开始,数千年辗转不知所终。1864年4月,时任直隶提督的淮军将领刘铭传,驻扎在常州太平天国护王陈坤书的王府中。午夜,万籁俱寂之时,突然传来金属悦耳的叩击声。刘铭传秉烛寻音,转到马厩之内,听到马笼头的铁环碰击马槽发出清脆的金属声。于是,他拨开草料,这件被用作马槽的稀世珍宝,终于重见天日。他将铜盘送回合肥老家,并专门盖亭收藏,轻易不肯示人。抗日战争时期,为了保护铜盘,其后人将它埋于地下一丈多深,才躲过了战乱。1950年元月,由其曾孙护盘进京,献于国家。从此,这件国宝一直珍藏在中国历史博物馆。
夕阳冉冉,依山面水,刘铭传墓园笼罩在一片落日余晖之中。牌楼庄严耸立,两侧对联:“凿山冶铁作驰道,俯海列炮屯坚营”,是摘自梁启超《游台湾追怀刘壮肃公》的诗句。大潜山东北之麓,刘铭传生平展馆收藏着大量文献资料,让更多人能深入了解其事功和精神。
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当法军的铁蹄侵入台湾之时,也把刘铭传推向了台湾的历史舞台。刘铭传临危受命,带领“铭”字营的江淮子弟以及台湾人民抗法保台,粉碎了侵略者吞占台海的企图,捍卫了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此一捷报中外报纸均大幅报道,是启发台湾精神的一道曙光,亦是烽火年代的珍贵欢欣。”我在馆藏资料中,读到时人如此动情的评价。
有清一代,特别是嘉道以后,淮军将领刘铭传、唐定奎等任职台湾,对海防形势的稳定和当地社会经济发展所起的积极作用,使得合肥与台湾的联系有着特殊的意义。中法战争的硝烟,让台湾作为东南沿海七省门户的战略地位更加凸显。l885年,清廷颁旨,台湾正式成为中国的一个省份,刘铭传被任命为首任巡抚。
作为台湾首任巡抚,刘铭传生前和身后的故事很多。在1885年至1891年的七年任期内,置定三府、一州、十一县、四厅,基本奠定了今天台湾地方行政区划的基础。创办新式学堂,“千万间大厦宏开,遍鹿岛鲲洋,多士从滋承教育;二百年斯文远绍,看鸾旗鼍鼓,诸君何以答升平?”练新军,开煤矿,办电讯,每一项都关乎民生,可以说,是台湾走向近代化的第一缕曙光。纪念馆展板上录有数则史家定评,台湾著名历史学家连横称之“溯其功业,足与台湾不朽矣”。
抚台新政,为开发台湾数百年之所未见,最值得称道的是台湾铁路的修建。他深知铁路是国家血脉,断不能听任外人垄断。1887年,刘铭传在台北设立铁路总局,经过将近四年的艰苦施工,台北至基隆段铁路于1891年竣工通车。“十五年生面独开,羽毂飙轮,从此康庄通海屿;三百丈岩腰新劈,云梯石栈,居然人力胜天工。”台湾铁路,是中国自行集资、自行兴建、自行控制的第一条铁路。纪念馆里陈列着复制的火车头,笛声鸣响,清亮激越,在琳琅满目的展厅久久回荡。
刘铭传对台湾的贡献、热爱已经深深地植根于两岸民心。今天,在台北市中心的新公园内,巍然矗立着刘铭传的铜像;为纪念其功绩,还特别设立铭传大学、铭传中学、铭传小学及刘铭传路。走进大潜山下的刘老圩,圩外门楣上写着“大潜山房”,一副“解甲归田乐,清时旧垒闲”的楹联,分列两旁。但他晚年归养故里,难得乐闲。展读他的《筹造折》,开篇即言:“每念中国大局,往往中夜起立,眦裂泣下”。忧患之情跃然纸上,后来的事件也证明他这种针对性极强的忧患意识是极可贵的。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签订,消息传来,得知自己一生中花最大精力创置的台湾省被割让给日本,刘铭传忧思郁结,悲愤交加,病情迅速恶化,病逝时留下《乙未冬绝笔》:“历尽艰危报主知,功成翻悔入山迟。平生一觉封侯梦,已到黄粱饭熟时。”
傍着逐渐清淡的晚晖,一路走来,碑石的苔痕斑驳,让我从触摸中感到一种来自历史深处的苍凉。不由得在心里感喟,刘铭传生于封建末世,眼见祖国被列强瓜分,力主变革图强,抵御外侮,举办洋务,希望民族振兴,国家强盛,在台湾近代化的过程中,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他的一片爱国热忱,是永远值得缅怀和纪念的。随后又想,他出身行伍,身处闭塞守旧的十九世纪末,何以有此异于常人的思想与识见?可以说,源自大潜山下的这方热土,必定给予他一生的精神滋养。刘铭传是海峡两岸的一种历史文化标识,实际上,在故乡的情感世界里,对于刘铭传的怀念,早已沉淀为某种特殊情愫。
大潜山上的巨大风轮,已淹没在黝黑的夜色中,看不见了。
夜空群星毕现,天地如此幽邃与辽阔,像一条割不断的河,静静地流淌。
十月的大潜山,层林尽染。繁茂苍郁中,豪门深宅的刘老圩,静静地矗立在山脚下。过外吊桥进圩,想不到还有一道内壕沟,依旧是绿水滔滔、吊桥和门楼,视野里才见气势恢宏的庭院。百年老宅,集防御、生活、休闲于一体,是淮军将领故里圩堡群的突出庄园风格,呈现出江淮之间一种独特的圩堡文化。
刘老圩始建于1868年,建筑均为排山排柱,雕梁画栋。一些厅堂的地基、石础倾塌在荒草中,被保护起来,没有原址复建,从中依然可以看出当年钟鸣鼎食、火树银花的气度与格局。
尽管原建筑现多不存,当年刘铭传亲手栽植的数十株广玉兰,至今仍然高大挺拔,蓊茂郁秀。而百年沧桑之间,古木还有神奇之处,两棵两棵地同根生长,仿佛同胞兄弟,并立参天。这样的一种植物,我还是有些惊奇的,端的很少见到。由此也想到天地间的一些事物,无论过去、未来和现在,从来就是一个整体,它们的根深深地扎于大地,内在的血肉联系是任何强力和意志都无法割裂的。
庭院深深几许。穿行于圩堡迂回的甬道,那份宁静神秘的气息依然存在。故居的西北有座霸王墩,为古人类遗址;东南的大堰波光潋滟,是当年取土烧砖瓦形成,那么大一片水面,能取多少土?能烧多少砖、盖多少楼?堰中有岛,上面是一座读书楼,无桥与外相通,彼岸送餐的小舟系在树上,无人自横。安心读书,有水月可看,有鸟鸣可听,有花树可依,而无衣食之忧、市声聒耳、琐碎烦神。这样大福,睡着都会笑醒了,只是哪里去找,何以修得?
盘亭四面环水,却有石桥可通,位于驱邪镇宅的“钢叉楼”的后面,是刘铭传专为陈列国宝虢季子白盘特地建造的。我上中学时随族爹写大字,《金文六种》最是头疼,“桓桓子白”总是篆不好,只是知道“四”字可以写成四横,像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一样欣喜。那是我第一次接触篆书。这次到刘老圩,我又知道了,虢季子白盘是我的乡贤从战火中保护下来的。说起来,我对金文的认知是从虢季子白盘开始的,这真是一种缘分。虢季子白盘,殷周时期盛水的青铜器,铸刻在底部的111个铭文,朴茂凝重,瑰丽奇伟,有着强烈的形式之美。
国宝多难,幸得刘铭传藏护,功莫大焉。从陕西宝鸡眉县出土的那一天开始,数千年辗转不知所终。1864年4月,时任直隶提督的淮军将领刘铭传,驻扎在常州太平天国护王陈坤书的王府中。午夜,万籁俱寂之时,突然传来金属悦耳的叩击声。刘铭传秉烛寻音,转到马厩之内,听到马笼头的铁环碰击马槽发出清脆的金属声。于是,他拨开草料,这件被用作马槽的稀世珍宝,终于重见天日。他将铜盘送回合肥老家,并专门盖亭收藏,轻易不肯示人。抗日战争时期,为了保护铜盘,其后人将它埋于地下一丈多深,才躲过了战乱。1950年元月,由其曾孙护盘进京,献于国家。从此,这件国宝一直珍藏在中国历史博物馆。
夕阳冉冉,依山面水,刘铭传墓园笼罩在一片落日余晖之中。牌楼庄严耸立,两侧对联:“凿山冶铁作驰道,俯海列炮屯坚营”,是摘自梁启超《游台湾追怀刘壮肃公》的诗句。大潜山东北之麓,刘铭传生平展馆收藏着大量文献资料,让更多人能深入了解其事功和精神。
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当法军的铁蹄侵入台湾之时,也把刘铭传推向了台湾的历史舞台。刘铭传临危受命,带领“铭”字营的江淮子弟以及台湾人民抗法保台,粉碎了侵略者吞占台海的企图,捍卫了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此一捷报中外报纸均大幅报道,是启发台湾精神的一道曙光,亦是烽火年代的珍贵欢欣。”我在馆藏资料中,读到时人如此动情的评价。
有清一代,特别是嘉道以后,淮军将领刘铭传、唐定奎等任职台湾,对海防形势的稳定和当地社会经济发展所起的积极作用,使得合肥与台湾的联系有着特殊的意义。中法战争的硝烟,让台湾作为东南沿海七省门户的战略地位更加凸显。l885年,清廷颁旨,台湾正式成为中国的一个省份,刘铭传被任命为首任巡抚。
作为台湾首任巡抚,刘铭传生前和身后的故事很多。在1885年至1891年的七年任期内,置定三府、一州、十一县、四厅,基本奠定了今天台湾地方行政区划的基础。创办新式学堂,“千万间大厦宏开,遍鹿岛鲲洋,多士从滋承教育;二百年斯文远绍,看鸾旗鼍鼓,诸君何以答升平?”练新军,开煤矿,办电讯,每一项都关乎民生,可以说,是台湾走向近代化的第一缕曙光。纪念馆展板上录有数则史家定评,台湾著名历史学家连横称之“溯其功业,足与台湾不朽矣”。
抚台新政,为开发台湾数百年之所未见,最值得称道的是台湾铁路的修建。他深知铁路是国家血脉,断不能听任外人垄断。1887年,刘铭传在台北设立铁路总局,经过将近四年的艰苦施工,台北至基隆段铁路于1891年竣工通车。“十五年生面独开,羽毂飙轮,从此康庄通海屿;三百丈岩腰新劈,云梯石栈,居然人力胜天工。”台湾铁路,是中国自行集资、自行兴建、自行控制的第一条铁路。纪念馆里陈列着复制的火车头,笛声鸣响,清亮激越,在琳琅满目的展厅久久回荡。
刘铭传对台湾的贡献、热爱已经深深地植根于两岸民心。今天,在台北市中心的新公园内,巍然矗立着刘铭传的铜像;为纪念其功绩,还特别设立铭传大学、铭传中学、铭传小学及刘铭传路。走进大潜山下的刘老圩,圩外门楣上写着“大潜山房”,一副“解甲归田乐,清时旧垒闲”的楹联,分列两旁。但他晚年归养故里,难得乐闲。展读他的《筹造折》,开篇即言:“每念中国大局,往往中夜起立,眦裂泣下”。忧患之情跃然纸上,后来的事件也证明他这种针对性极强的忧患意识是极可贵的。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签订,消息传来,得知自己一生中花最大精力创置的台湾省被割让给日本,刘铭传忧思郁结,悲愤交加,病情迅速恶化,病逝时留下《乙未冬绝笔》:“历尽艰危报主知,功成翻悔入山迟。平生一觉封侯梦,已到黄粱饭熟时。”
傍着逐渐清淡的晚晖,一路走来,碑石的苔痕斑驳,让我从触摸中感到一种来自历史深处的苍凉。不由得在心里感喟,刘铭传生于封建末世,眼见祖国被列强瓜分,力主变革图强,抵御外侮,举办洋务,希望民族振兴,国家强盛,在台湾近代化的过程中,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他的一片爱国热忱,是永远值得缅怀和纪念的。随后又想,他出身行伍,身处闭塞守旧的十九世纪末,何以有此异于常人的思想与识见?可以说,源自大潜山下的这方热土,必定给予他一生的精神滋养。刘铭传是海峡两岸的一种历史文化标识,实际上,在故乡的情感世界里,对于刘铭传的怀念,早已沉淀为某种特殊情愫。
大潜山上的巨大风轮,已淹没在黝黑的夜色中,看不见了。
夜空群星毕现,天地如此幽邃与辽阔,像一条割不断的河,静静地流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