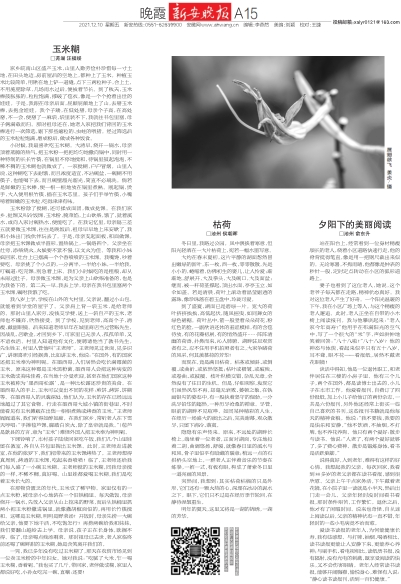发布日期:
玉米糊
□芜湖汪福绥
家乡皖南山区盛产玉米,山里人勤劳俭朴珍惜每一寸土地,在田头地边,房前屋后的空地上,都种上了玉米。种植玉米比较简单,用锹在地上铲一道缝,点下三两粒种子,合上土,不用施肥除草,几场雨水过后,便拔着节长。到了秋天,玉米棒鼓胀胀的,粒粒饱满,撑破了苞衣,像是一个个抢着出世的娃娃。于是,我跟在母亲后面,屁颠屁颠地上了山,去掰玉米棒,去抱金娃娃。我个子矮,在低处掰,母亲个子高,在高处掰,不一会,便掰了一麻袋,袋里装不下,我就往书包里塞,母子俩满载而归。那时祖母还在,她老人家把我们背回的玉米棒进行一次筛选,剔下那些瘪粒的、虫蛀的喂猪。经过筛选后的玉米粒粒饱满,磨成粉后,做成各种饭食。
小时候,我最喜欢吃玉米糊。大清早,烧开一锅水,母亲顶着蒸腾的热气,把玉米粉一把把均匀地撒向锅中,同时用一种特制的长长竹筷,在锅里不停地搅和,待锅里鼓起泡泡,不稀不稠的玉米糊也就做成了。一家搅糊,户户冒烟。山里人说,这种糊吃下去耐饿,而且浓度适宜,不沾碗盆,一碗糊不用筷子,也能喝下去,而且碗壁溜光溜光,简直不必刷洗。倘若是鲜嫩的玉米棒,便一根一根地放在锅里煮熟。刚起锅,烫手,大人便用根竹筷,插在玉米芯里。孩子们手举竹筷,小嘴啃着鲜嫩的玉米粒,吃得津津有味。
玉米粉除了搅糊,还可揉成面团,做成挞馃。在我们家乡,挞馃又叫冷饭馃,玉米粉,腌菜馅,上山砍柴,饿了,就着溪水,或向人家讨碗热水,便能吃了。在我记忆里,母亲隔三差五就要做玉米馃,往往是晚饭后,祖母早早地上床安歇了,我和小妹出门找伙伴玩去了。于是,母亲支起面板,和面做馃。母亲把玉米馃做成半圆形,置热锅上,一锅烙四个。父亲坐在灶旁,添柴烧火,火候要不紧不慢,以文火为佳。等我和小妹疯回家,灶台上已摆满一个个香喷喷的玉米馃。我嘴馋,吵着要吃。母亲挑了个小点的,一分两半,一半给小妹,一半给我,叮嘱道:吃完馃,别急着上床。我们小时候吃的是粗粮,却从未闹过肚子。母亲做玉米馃,是为父亲上山砍柴准备的,也是为我备下的。第二天一早,我去上学,母亲在我书包里塞两个玉米馃,嘱咐我饿了吃。
我八岁上学,学校在山外的大村里,父亲说,翻过小山包,就能看到学堂的屋宇了。父亲肩上背一袋玉米,是给老师的。那时山里人家穷,没钱交学费,送上一袋自产的玉米,老师也不嫌弃,欣然接受。到了学校,见到老师,高高个子,清瘦,戴副眼镜。后来知道老师早年在城里商店当过管账先生,因战乱,店歇业,才回到乡下,可家里已无亲人,孤孤单单,又不谙农活。村里人知道他有文化,便聘请他当了教书先生。先生姓王,村里人管他叫“王老师”。王老师见过世面,见多识广,讲课喜欢引经据典,比如讲玉米,他说:“在国外,有的国家还把玉米奉为神明呢。在墨西哥,人们居然会吃长满霉菌的玉米。原来这种霉是玉米黑粉菌,墨西哥人会把这种病变的玉米做成美味佳肴,在当地十分受欢迎,甚至在他们国家这种玉米被称为‘墨西哥松露’,是一种比松露还珍贵的美食。在墨西哥人的手上,玉米可以变出不同的花样:煎饼、烤饼、饼糊等。在墨西哥人的灵魂深处,他们认为,玉米的存在已经远远地超过了其它食物。行走在墨西哥大城小镇的街巷里,不时能看见有玉米摊贩在出售一根根煮熟或烤香的玉米。”王老师娓娓道来,我们听得如醉如痴。在我们家乡,常听老人在下雪天哼唱:“手捧苞芦馃,脚踏白炭火,除了皇帝就是我。”(苞芦是歙县的方言,意为“玉米”)难怪外国人把玉米奉为神明呢。
下课铃响了,本村孩子陆续回家吃午饭,我们几个山里娃留在教室,各自从书包里掏出玉米馃。此时,王老师走进教室,在他的张罗下,我们把带来的玉米馃烤热了。王老师想得真周到,烤透的玉米馃,吃起来香喷喷!临了,王老师还给我们每人盛了一小碗玉米糊。王老师搅的玉米糊,同我母亲搅的一样,不稀不稠,真好喝。山里娃都爱喝玉米糊,我们是吃着玉米长大的。
在那物资匮乏的年代,玉米成了稀罕物。家里仅有的一点玉米粉,被母亲小心地装在一个旧铁桶里。每天做饭,母亲烧开一锅水,先放入父亲从山上挖来的野菜,而后从铁桶里抓两小把玉米粉撒进锅里,就像撒胡椒面似的,再用长竹筷搅和。这哪是玉米糊,明明是野菜汤!开饭时,母亲先捞一大碗给父亲,他要下地干活,不吃饱怎行?再捞两碗给我和妹妹,我们要翻山越岭去上学。母亲说,孩子正在长身体,耽搁不得。临了,母亲喝点残汤剩菜。那时祖母已去世,老人家临终前还喝了碗鲜甜的玉米糊,她是含笑离开我们的。
一晃,我已多年没有吃过玉米糊了,那天在农贸市场见到一位卖玉米粉的中年妇女。她对我说:“吃腻了大米,乍一喝玉米糊,香着呢。”我也买了几斤,带回家,老伴做成糊,家里人都说好吃,小孙女吃完一碗,直嚷:还要!
家乡皖南山区盛产玉米,山里人勤劳俭朴珍惜每一寸土地,在田头地边,房前屋后的空地上,都种上了玉米。种植玉米比较简单,用锹在地上铲一道缝,点下三两粒种子,合上土,不用施肥除草,几场雨水过后,便拔着节长。到了秋天,玉米棒鼓胀胀的,粒粒饱满,撑破了苞衣,像是一个个抢着出世的娃娃。于是,我跟在母亲后面,屁颠屁颠地上了山,去掰玉米棒,去抱金娃娃。我个子矮,在低处掰,母亲个子高,在高处掰,不一会,便掰了一麻袋,袋里装不下,我就往书包里塞,母子俩满载而归。那时祖母还在,她老人家把我们背回的玉米棒进行一次筛选,剔下那些瘪粒的、虫蛀的喂猪。经过筛选后的玉米粒粒饱满,磨成粉后,做成各种饭食。
小时候,我最喜欢吃玉米糊。大清早,烧开一锅水,母亲顶着蒸腾的热气,把玉米粉一把把均匀地撒向锅中,同时用一种特制的长长竹筷,在锅里不停地搅和,待锅里鼓起泡泡,不稀不稠的玉米糊也就做成了。一家搅糊,户户冒烟。山里人说,这种糊吃下去耐饿,而且浓度适宜,不沾碗盆,一碗糊不用筷子,也能喝下去,而且碗壁溜光溜光,简直不必刷洗。倘若是鲜嫩的玉米棒,便一根一根地放在锅里煮熟。刚起锅,烫手,大人便用根竹筷,插在玉米芯里。孩子们手举竹筷,小嘴啃着鲜嫩的玉米粒,吃得津津有味。
玉米粉除了搅糊,还可揉成面团,做成挞馃。在我们家乡,挞馃又叫冷饭馃,玉米粉,腌菜馅,上山砍柴,饿了,就着溪水,或向人家讨碗热水,便能吃了。在我记忆里,母亲隔三差五就要做玉米馃,往往是晚饭后,祖母早早地上床安歇了,我和小妹出门找伙伴玩去了。于是,母亲支起面板,和面做馃。母亲把玉米馃做成半圆形,置热锅上,一锅烙四个。父亲坐在灶旁,添柴烧火,火候要不紧不慢,以文火为佳。等我和小妹疯回家,灶台上已摆满一个个香喷喷的玉米馃。我嘴馋,吵着要吃。母亲挑了个小点的,一分两半,一半给小妹,一半给我,叮嘱道:吃完馃,别急着上床。我们小时候吃的是粗粮,却从未闹过肚子。母亲做玉米馃,是为父亲上山砍柴准备的,也是为我备下的。第二天一早,我去上学,母亲在我书包里塞两个玉米馃,嘱咐我饿了吃。
我八岁上学,学校在山外的大村里,父亲说,翻过小山包,就能看到学堂的屋宇了。父亲肩上背一袋玉米,是给老师的。那时山里人家穷,没钱交学费,送上一袋自产的玉米,老师也不嫌弃,欣然接受。到了学校,见到老师,高高个子,清瘦,戴副眼镜。后来知道老师早年在城里商店当过管账先生,因战乱,店歇业,才回到乡下,可家里已无亲人,孤孤单单,又不谙农活。村里人知道他有文化,便聘请他当了教书先生。先生姓王,村里人管他叫“王老师”。王老师见过世面,见多识广,讲课喜欢引经据典,比如讲玉米,他说:“在国外,有的国家还把玉米奉为神明呢。在墨西哥,人们居然会吃长满霉菌的玉米。原来这种霉是玉米黑粉菌,墨西哥人会把这种病变的玉米做成美味佳肴,在当地十分受欢迎,甚至在他们国家这种玉米被称为‘墨西哥松露’,是一种比松露还珍贵的美食。在墨西哥人的手上,玉米可以变出不同的花样:煎饼、烤饼、饼糊等。在墨西哥人的灵魂深处,他们认为,玉米的存在已经远远地超过了其它食物。行走在墨西哥大城小镇的街巷里,不时能看见有玉米摊贩在出售一根根煮熟或烤香的玉米。”王老师娓娓道来,我们听得如醉如痴。在我们家乡,常听老人在下雪天哼唱:“手捧苞芦馃,脚踏白炭火,除了皇帝就是我。”(苞芦是歙县的方言,意为“玉米”)难怪外国人把玉米奉为神明呢。
下课铃响了,本村孩子陆续回家吃午饭,我们几个山里娃留在教室,各自从书包里掏出玉米馃。此时,王老师走进教室,在他的张罗下,我们把带来的玉米馃烤热了。王老师想得真周到,烤透的玉米馃,吃起来香喷喷!临了,王老师还给我们每人盛了一小碗玉米糊。王老师搅的玉米糊,同我母亲搅的一样,不稀不稠,真好喝。山里娃都爱喝玉米糊,我们是吃着玉米长大的。
在那物资匮乏的年代,玉米成了稀罕物。家里仅有的一点玉米粉,被母亲小心地装在一个旧铁桶里。每天做饭,母亲烧开一锅水,先放入父亲从山上挖来的野菜,而后从铁桶里抓两小把玉米粉撒进锅里,就像撒胡椒面似的,再用长竹筷搅和。这哪是玉米糊,明明是野菜汤!开饭时,母亲先捞一大碗给父亲,他要下地干活,不吃饱怎行?再捞两碗给我和妹妹,我们要翻山越岭去上学。母亲说,孩子正在长身体,耽搁不得。临了,母亲喝点残汤剩菜。那时祖母已去世,老人家临终前还喝了碗鲜甜的玉米糊,她是含笑离开我们的。
一晃,我已多年没有吃过玉米糊了,那天在农贸市场见到一位卖玉米粉的中年妇女。她对我说:“吃腻了大米,乍一喝玉米糊,香着呢。”我也买了几斤,带回家,老伴做成糊,家里人都说好吃,小孙女吃完一碗,直嚷:还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