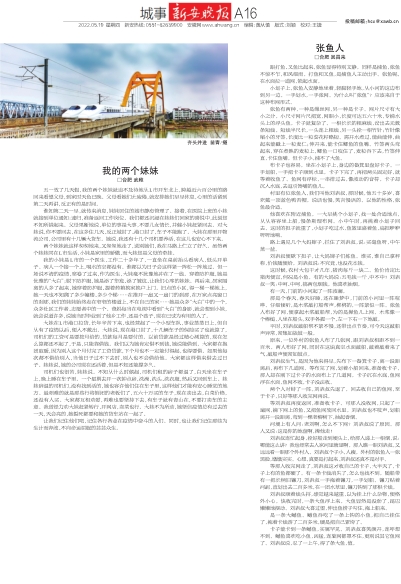发布日期:
张鱼人
□合肥吴昌来
跟打鱼、叉鱼比起来,张鱼显得特别文静。同样是捕鱼,张鱼不惊不乍,和风细雨。打鱼和叉鱼,是捕鱼人主动出手。张鱼呢,在水面拉一道网,锁起水面。
小划子上,张鱼人安静地坐着,轻脚轻手地,从小河的这边布到另一边。一手划水,一手张网。为什么叫“张鱼”?应该来自于这种布网形式。
张鱼有两种,一种是缫丝网,另一种是卡子。网片尺寸有大小之分。小尺寸网片尺把宽,网眼小,长度可达五六十米,专捕水头上的浮头鱼。卡子就复杂了。一根长长的粗麻线,岔出去无数条短线。短线半尺长,一头连上粗线,另一头拴一根竹针;竹针像缩小的牙签,长度比一粒葵花籽略短。需开水煮过,能曲能伸,曲起来能戳上一粒麦仁;伸开来,能卡住鲫鱼的鱼嘴。竹签两头弯起来,穿在煮熟的麦粒上,鲫鱼一口咬住了,麦粒吞下去,竹签伸直,卡住鱼嘴。但卡子小,捕不了大鱼。
布卡子也容易。坐在小划子上,身边的畚箕里盘好卡子。一手划船,一手把卡子顺到水里。卡子下完了,再把两头固定好,就等着收鱼了。鱼网有浮标,一串排过去,像波动的音符。卡子却沉入水底,去逗引馋嘴的鱼儿。
村里有位张鱼人,我们叫他刘表叔,那时候,他五十多岁,喜欢戴一顶蓝色鸭舌帽。说话也慢,笑言慢语的。以他的性格,张鱼最合适。
他喜欢在附近捕鱼。一大早挑个小划子,找一处合适地点,从从容容坐上船,慢条斯理布网。小中午时,再挑着小划子回去。这时的担子就重了,小划子吃过水,鱼篮里盛着鱼,扁担咿咿呀呀地响。
路上遇见几个大妈婶子,拦住了刘表叔,说:买毫鱼呀,中午蒸一盆。
刘表叔便歇下担子,让大妈婶子们拣鱼。谁买,谁自己拿秤称,价钱随便给。刘表叔说:不究竟,也没花本钱。
这时候,农村大包干才几年,猪肉每斤一块二。鱼价肯定比猪肉便宜,何况是小鱼。有的大妈说:五毛钱一斤,中不中?刘表叔一笑:中呵、中呵,搞两包烟钱。他喜欢抽烟。
有一天,门前的小河起了一阵波澜。
那是个春天,春天好睡,还在睡梦中,门前的小河里一阵喧哗。仔细倾听,是木桨敲打船帮声,梆梆的,一阵紧似一阵。张鱼人布好了网,便拿起木桨敲船帮,为的是撵鱼儿上网。木桨像一个棒槌,人坐在船头,双手各握一个,左一下右一下地敲。
平时,刘表叔敲船帮不紧不慢,还带出点节奏,可今天这敲船声异常,密集如战鼓一般。
原来,一位外村的张鱼人布了几张网,跟刘表叔相距不到一百米。两人布好了网,同时在这块真空水面敲船,敲着敲着来了气,敲船声便密如鼓点。
刘表叔生气,是因为他来得早,先布下一畚箕卡子,离一段距离后,再布下几道网。等布完了网,划着小船回来,准备收卡子,那人却在刚下过卡子的水面布上了几道网。卡子沉在水底,鱼网浮在水面,鱼网不收,卡子没法收。
两个人对峙了一阵,刘表叔先退了。回去收自己的鱼网,至于卡子,只好等那人收完网再说。
等刘表叔再度返回,准备收卡子。可那人没收网,只起了一遍网,摘下网上的鱼,又把鱼网放回水里。刘表叔也不吱声,划船离开一段距离,弯到一棵老柳树下,抽起香烟。
河埂上有人问:老刘啊,怎么不下网?刘表叔说了原因。那人又说:这是你的地盘啊,撵他走!
刘表叔连忙起身,拴好船走到埂头上,给那人递上一根烟,说:哪能这么讲?我也经常去人家河里塘里啊。那人瞧一眼刘表叔,又远远看一眼那个外村人。刘表叔个子小,人瘦。外村的张鱼人一张黑脸,墩墩实实。心想,真要是打起来,刘表叔还真不是对手。
等那人收完网走了,刘表叔这才收自己的卡子,大半天了,卡子上有的鱼都硬了。有一条卡线消失了,怎么也找不到。随船带有一把长柄旧镰刀,刘表叔一手拖着镰刀,一手划船。镰刀贴着河泥,直划出去二百多米,在一团水草里,镰刀钩到了那根卡线。
刘表叔顺着线头捋,感觉越来越重,以为挂上什么杂物,便格外小心。快收完时,一条大鱼浮上来。大鱼显然是没劲了,尾巴懒懒地摆动。刘表叔大喜过望,伸出鱼捞子勾住,拖上船来。
是一条大鳡鱼。鳡鱼吞吃了一条上钩的小鱼,把自己挂住了,拖着卡线游了二百多米,硬是把自己累垮了。
卡子能卡到一条鳡鱼,实属罕见。刘表叔喜笑颜开,连呼想不到。鳡鱼喜欢吃小鱼,凶猛,连旋网都罩不住,更别说其它鱼网了。刘表叔说,忍了一上午,得了条大鱼,值。
跟打鱼、叉鱼比起来,张鱼显得特别文静。同样是捕鱼,张鱼不惊不乍,和风细雨。打鱼和叉鱼,是捕鱼人主动出手。张鱼呢,在水面拉一道网,锁起水面。
小划子上,张鱼人安静地坐着,轻脚轻手地,从小河的这边布到另一边。一手划水,一手张网。为什么叫“张鱼”?应该来自于这种布网形式。
张鱼有两种,一种是缫丝网,另一种是卡子。网片尺寸有大小之分。小尺寸网片尺把宽,网眼小,长度可达五六十米,专捕水头上的浮头鱼。卡子就复杂了。一根长长的粗麻线,岔出去无数条短线。短线半尺长,一头连上粗线,另一头拴一根竹针;竹针像缩小的牙签,长度比一粒葵花籽略短。需开水煮过,能曲能伸,曲起来能戳上一粒麦仁;伸开来,能卡住鲫鱼的鱼嘴。竹签两头弯起来,穿在煮熟的麦粒上,鲫鱼一口咬住了,麦粒吞下去,竹签伸直,卡住鱼嘴。但卡子小,捕不了大鱼。
布卡子也容易。坐在小划子上,身边的畚箕里盘好卡子。一手划船,一手把卡子顺到水里。卡子下完了,再把两头固定好,就等着收鱼了。鱼网有浮标,一串排过去,像波动的音符。卡子却沉入水底,去逗引馋嘴的鱼儿。
村里有位张鱼人,我们叫他刘表叔,那时候,他五十多岁,喜欢戴一顶蓝色鸭舌帽。说话也慢,笑言慢语的。以他的性格,张鱼最合适。
他喜欢在附近捕鱼。一大早挑个小划子,找一处合适地点,从从容容坐上船,慢条斯理布网。小中午时,再挑着小划子回去。这时的担子就重了,小划子吃过水,鱼篮里盛着鱼,扁担咿咿呀呀地响。
路上遇见几个大妈婶子,拦住了刘表叔,说:买毫鱼呀,中午蒸一盆。
刘表叔便歇下担子,让大妈婶子们拣鱼。谁买,谁自己拿秤称,价钱随便给。刘表叔说:不究竟,也没花本钱。
这时候,农村大包干才几年,猪肉每斤一块二。鱼价肯定比猪肉便宜,何况是小鱼。有的大妈说:五毛钱一斤,中不中?刘表叔一笑:中呵、中呵,搞两包烟钱。他喜欢抽烟。
有一天,门前的小河起了一阵波澜。
那是个春天,春天好睡,还在睡梦中,门前的小河里一阵喧哗。仔细倾听,是木桨敲打船帮声,梆梆的,一阵紧似一阵。张鱼人布好了网,便拿起木桨敲船帮,为的是撵鱼儿上网。木桨像一个棒槌,人坐在船头,双手各握一个,左一下右一下地敲。
平时,刘表叔敲船帮不紧不慢,还带出点节奏,可今天这敲船声异常,密集如战鼓一般。
原来,一位外村的张鱼人布了几张网,跟刘表叔相距不到一百米。两人布好了网,同时在这块真空水面敲船,敲着敲着来了气,敲船声便密如鼓点。
刘表叔生气,是因为他来得早,先布下一畚箕卡子,离一段距离后,再布下几道网。等布完了网,划着小船回来,准备收卡子,那人却在刚下过卡子的水面布上了几道网。卡子沉在水底,鱼网浮在水面,鱼网不收,卡子没法收。
两个人对峙了一阵,刘表叔先退了。回去收自己的鱼网,至于卡子,只好等那人收完网再说。
等刘表叔再度返回,准备收卡子。可那人没收网,只起了一遍网,摘下网上的鱼,又把鱼网放回水里。刘表叔也不吱声,划船离开一段距离,弯到一棵老柳树下,抽起香烟。
河埂上有人问:老刘啊,怎么不下网?刘表叔说了原因。那人又说:这是你的地盘啊,撵他走!
刘表叔连忙起身,拴好船走到埂头上,给那人递上一根烟,说:哪能这么讲?我也经常去人家河里塘里啊。那人瞧一眼刘表叔,又远远看一眼那个外村人。刘表叔个子小,人瘦。外村的张鱼人一张黑脸,墩墩实实。心想,真要是打起来,刘表叔还真不是对手。
等那人收完网走了,刘表叔这才收自己的卡子,大半天了,卡子上有的鱼都硬了。有一条卡线消失了,怎么也找不到。随船带有一把长柄旧镰刀,刘表叔一手拖着镰刀,一手划船。镰刀贴着河泥,直划出去二百多米,在一团水草里,镰刀钩到了那根卡线。
刘表叔顺着线头捋,感觉越来越重,以为挂上什么杂物,便格外小心。快收完时,一条大鱼浮上来。大鱼显然是没劲了,尾巴懒懒地摆动。刘表叔大喜过望,伸出鱼捞子勾住,拖上船来。
是一条大鳡鱼。鳡鱼吞吃了一条上钩的小鱼,把自己挂住了,拖着卡线游了二百多米,硬是把自己累垮了。
卡子能卡到一条鳡鱼,实属罕见。刘表叔喜笑颜开,连呼想不到。鳡鱼喜欢吃小鱼,凶猛,连旋网都罩不住,更别说其它鱼网了。刘表叔说,忍了一上午,得了条大鱼,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