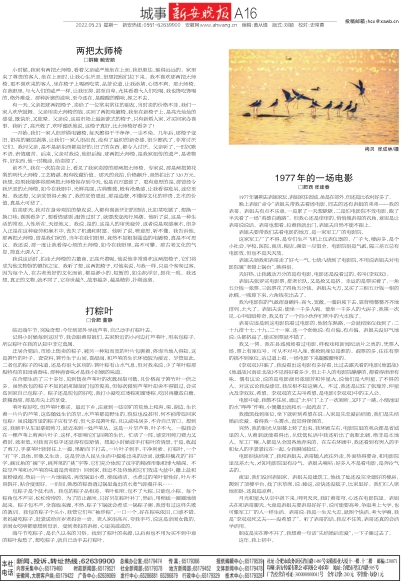发布日期:
打粽叶
□合肥董静
临近端午节,突发奇想:今年到郊外寻找芦苇,自己动手打粽叶去。
记得小时候每到这时节,我会跟着哥姐们,去家附近的小河边打芦苇叶,用来包粽子,所以粽叶在我的认知中非它莫属。
迁居合肥后,市场上售卖的粽子,被另一种短而宽的叶片包裹着,咨询当地人得知,这是箬竹的叶子。查资料,箬竹生于山间,喜湿润,和芦苇的生长环境较为接近。尽管如此,二者包的粽子的味道,还是有很大区别的:箬叶粽有山水气息,但对我来说,少了苇叶粽那股特有的田园清香味,那种清香味才是我小时候的味道。
在合肥生活了三十多年,见到售卖芦苇叶的次数屈指可数,且价格高于箬竹叶一倍之多。虽然我包的粽子不如妈妈和姐姐们包的俊美,但每次碰到芦苇叶却舍不得错过,会买些回家自己包粽子。粽子还是现包的好吃,我打小爱吃红枣粽和蜜枣粽,吃时再撒些白糖,软糯香甜,那是舌尖上的享受。
苇叶粽好吃,但芦苇叶难买。最近下乡,注意到一些空旷的荒地上和沟、渠、湖边,生长着一片片的芦苇,这些随处生长的旱、水芦苇都是野生的,貌似也没甚用,何不捎带些回家包粽?虽说超市里的粽子应有尽有,但大多是箬叶粽,且以咸味居多,不合自己胃口。想到这,我顺手从车里拿把剪刀,就近来到一处芦苇丛。这是一片旱芦苇,叶子不大。一般我会在一棵芦苇上剪两片叶子,这样,不影响它们后期的生长。忙活了一阵,感觉用剪刀费力又费时,效率低,对我而言似乎还显得有些矫情。想起小时候徒手打粽叶的情景,于是,收起了剪刀,手拿苇叶轻轻往上一提,果断向下打去,一片叶子到手,干净利索。打粽叶,一个“打”字,具体、形象又生动。这是劳动人民从生活中提炼出来的动词,就像捋槐花的“捋”字、摘豆角的“摘”字、挑荠菜的“挑”字等,它们充分体现了汉字的精准形象和博大精深。不知旱芦苇和水芦苇的味道是否相同?回到家,我迫不及待地把它们放进大盆中,撒上盐和面粉浸泡,然后一片一片地刷洗,再放锅里小煮,彻底清洁。水煮过的苇叶韧性好,叶片不易裂开,贴合度更好。一时间,熟悉的粽香透过锅里逸出的水蒸气弥漫开来……
包粽子是个技术活。我包的粽子品相差。苇叶细窄,包不了大粽,只能包小粽。每个粽角包不严实,松松垮垮的。为了防止漏米,只好另加粽叶补丁,然后,用棉线一圈圈地绕起来。粽子包不严,全靠线来缠,不然,粽子下锅就会煮成一锅粽子粥,我曾有过这样失败的教训。我包的粽子个头小,我管它们叫“袖珍粽”,一口一个,好在粽味依旧,口感不错。老妈爱吃粽子,赶紧送给百岁老妈尝一尝。老人家很高兴,夸我手巧,说这是亲闺女做的,亲闺女吃啥都能想到母亲。受到老妈的表扬,心里美滋滋的。
端午节吃粽子,是长久以来的习俗。找到了粽叶的来源,以后再也不用为买不到中意的粽叶发愁了,想吃粽子,就自己动手去打粽叶。
临近端午节,突发奇想:今年到郊外寻找芦苇,自己动手打粽叶去。
记得小时候每到这时节,我会跟着哥姐们,去家附近的小河边打芦苇叶,用来包粽子,所以粽叶在我的认知中非它莫属。
迁居合肥后,市场上售卖的粽子,被另一种短而宽的叶片包裹着,咨询当地人得知,这是箬竹的叶子。查资料,箬竹生于山间,喜湿润,和芦苇的生长环境较为接近。尽管如此,二者包的粽子的味道,还是有很大区别的:箬叶粽有山水气息,但对我来说,少了苇叶粽那股特有的田园清香味,那种清香味才是我小时候的味道。
在合肥生活了三十多年,见到售卖芦苇叶的次数屈指可数,且价格高于箬竹叶一倍之多。虽然我包的粽子不如妈妈和姐姐们包的俊美,但每次碰到芦苇叶却舍不得错过,会买些回家自己包粽子。粽子还是现包的好吃,我打小爱吃红枣粽和蜜枣粽,吃时再撒些白糖,软糯香甜,那是舌尖上的享受。
苇叶粽好吃,但芦苇叶难买。最近下乡,注意到一些空旷的荒地上和沟、渠、湖边,生长着一片片的芦苇,这些随处生长的旱、水芦苇都是野生的,貌似也没甚用,何不捎带些回家包粽?虽说超市里的粽子应有尽有,但大多是箬叶粽,且以咸味居多,不合自己胃口。想到这,我顺手从车里拿把剪刀,就近来到一处芦苇丛。这是一片旱芦苇,叶子不大。一般我会在一棵芦苇上剪两片叶子,这样,不影响它们后期的生长。忙活了一阵,感觉用剪刀费力又费时,效率低,对我而言似乎还显得有些矫情。想起小时候徒手打粽叶的情景,于是,收起了剪刀,手拿苇叶轻轻往上一提,果断向下打去,一片叶子到手,干净利索。打粽叶,一个“打”字,具体、形象又生动。这是劳动人民从生活中提炼出来的动词,就像捋槐花的“捋”字、摘豆角的“摘”字、挑荠菜的“挑”字等,它们充分体现了汉字的精准形象和博大精深。不知旱芦苇和水芦苇的味道是否相同?回到家,我迫不及待地把它们放进大盆中,撒上盐和面粉浸泡,然后一片一片地刷洗,再放锅里小煮,彻底清洁。水煮过的苇叶韧性好,叶片不易裂开,贴合度更好。一时间,熟悉的粽香透过锅里逸出的水蒸气弥漫开来……
包粽子是个技术活。我包的粽子品相差。苇叶细窄,包不了大粽,只能包小粽。每个粽角包不严实,松松垮垮的。为了防止漏米,只好另加粽叶补丁,然后,用棉线一圈圈地绕起来。粽子包不严,全靠线来缠,不然,粽子下锅就会煮成一锅粽子粥,我曾有过这样失败的教训。我包的粽子个头小,我管它们叫“袖珍粽”,一口一个,好在粽味依旧,口感不错。老妈爱吃粽子,赶紧送给百岁老妈尝一尝。老人家很高兴,夸我手巧,说这是亲闺女做的,亲闺女吃啥都能想到母亲。受到老妈的表扬,心里美滋滋的。
端午节吃粽子,是长久以来的习俗。找到了粽叶的来源,以后再也不用为买不到中意的粽叶发愁了,想吃粽子,就自己动手去打粽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