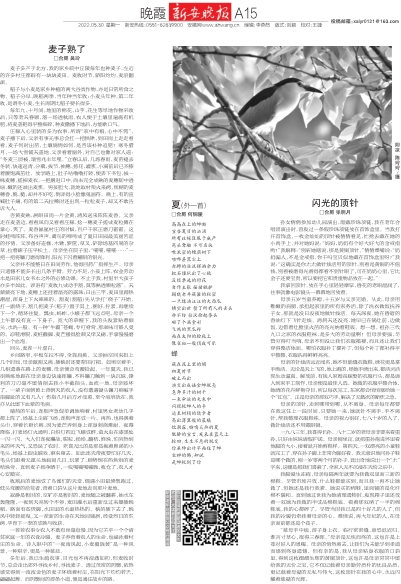发布日期:
麦子熟了
□合肥吴玲
麦子多产于北方,我的家乡皖中丘陵每年也种麦子,左近的许多村庄都辟有一块块麦田。麦收时节,骄阳灼灼,麦浪翻滚。
稻子与小麦是家乡种植的两大谷类作物,亦是日常所食之物。稻子分早、晚稻两季,当年种当年收;小麦头年种,第二年收,是谓冬小麦,生长周期比稻子要长得多。
每年九、十月间,地里的棉花、山芋、花生等旱地作物采收后,只等老天眷顾,落一场透秋雨,农人便于土壤里遍施有机肥,将麦垄耙得平整细碎,种麦撒播下地后,方能歇口气。
庄稼人心里装的多为农事,所谓“家中有粮,心中不慌”。麦子播下后,父亲有事无事总会扛一把铁锹,到田岗上走走看看,麦子何时出苗,土壤墒情如何,是否该补种追肥?寒冬腊月,一场大雪铺天盖地,父亲看着窗外,对自己也像对家人道:“冬麦三层被,瑞雪兆丰年哩。”立春以后,几场春雨,麦苗褪去冬装,快速返青,分蘖、拔节、抽穗、扬花、灌浆,小满前后已齐膝着腰饱满茁壮。放学路上,肚子咕噜噜打转,便丢下书包,拔一株麦穗,搓掉麦衣,一把撂进口中,尚未完全成熟的麦穗韧中透绿,嫩的还滋出麦浆。男孩胆大,就地取材架火来烤,焦糊的麦穗香、脆、糙,却并不好吃,倒弄得小脸像鬼画符。晚上,有的直喊肚子痛,有的第二天拉稀时还出现一粒粒麦子,却又不敢告诉大人。
杏黄麦熟,展眼田岗一片金黄,清风送来阵阵麦香。父亲走在麦垄边,看看风向又看看庄稼,捻一穗麦子搓成麦粒摊在掌心,笑了。麦香氤氲村庄的时候,百户千家正磨刀霍霍。这时蛙鸣阵阵,布谷声声,禽鸟的啼鸣成了夏日田园最美丽苦涩的抒情。父亲备好连枷、木锨、箩筐、草叉,铲除场基四周的杂草,拉着磙子压平松土。母亲坐在院子里,“嚯嚯,嚯嚯……”一把一把将镰刀磨得锋利,阳光下闪着耀眼的银光。
父亲并不能整日在田间劳作,他得回药厂指挥生产。母亲只遗憾不能多长出几条手臂。劳力不足,小孩上阵,农业劳动本是田家儿女书本之外的必修功课。不止于我,村里半大孩子亦多半如此。谚语有“麦收九成动手割,莫等熟透颗粒落”。天蒙蒙亮下地,麦穗上还挂着晶亮的露珠;日出三竿,麦田里溽热潮湿,浑身上下火辣辣的。割麦(割稻)先从学打“绕子”开始。打一副绕子,割几把麦子(稻子)置于其上,捆好,拧紧,再继续下一个,循环往复。瓢虫、蚂蚱、小蛾子都飞远点吧,母亲一个上午都没有直一下身子。宽大的草帽下,我的头发紧贴着额头,水洗一般。有一种“牛霸”苍蝇,专叮脊背,那滋味可够人受的。凉鞋滑脱,麦桩戳脚,麦芒搔得脸颊又痒又痛,手掌慢慢磨出一个血泡。
回头,麦茬一片虚白。
乡间路窄,平板车拉不得,全靠肩挑。父亲抽空回来担上几个时辰,母亲既割又挑,插秧时还要犁田打耙。如果空着手,几根遗落在路上的麦穗,母亲便会弯腰捡起。一年夏天,我已很熟练地跟在母亲身边快速挥镰,不料镰刀触到一块瓦砾,锋利的刀刃毫不留情削去我小半截指头,血流一地,母亲骇坏了。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人,没有遭遇锄头镰刀剜破手指脚趾的又有几人?伤指几月后方才痊愈,至今疤痕犹在,我亦从此留下血晕的毛病。
晴热的午后,连枷声急促单调地响着,村里男女老幼几乎都上阵了,场基上尘屑飞扬,连枷声连成一片。再热,也得裹着头巾,穿着长褂长裤,因为麦芒弄到身上浑身刺挠难耐。夜幕降临,打麦场灯火通明,白炽灯四近飞蛾成群,萤火虫在漆黑处一闪一闪。大人们连夜鏖战,脱粒、扬场、翻秸、堆垛,怕突然到来的坏天气,又恐误了农时。欢喜无比的是那些拖着鼻涕的小毛头,场基上捉虫嬉戏,窜来窜去。如此连天带夜要忙好几天,毛头们跟着无厘头地疯闹几日,玩累了,顺势倒在热烘烘的麦秸垛旁。直到麦子扬净晒干,一咬嘎嘣嘎嘣脆,收仓了,农人才心安踏实。
收割后的麦地成了鸟雀们的天堂,偶遇小田鼠倏忽跑过,低头弯腰的拾荒者,背着口袋从这片麦地走向那片麦地。
寂静是暂时的,空旷亦是暂时的,麦地随之被翻耕,抽水车轰隆隆,一夜到天亮转个不停,麦田灌水后重新反过来播插晚稻。路面有些烫脚,水田里的水温热热的。秧苗插下去了,晚风中轻轻摇曳,又一茬新的生命在天地间铺展,经受烈日的炙烤,孕育下一季的成熟与收获。
一茬茬农事令农人不敢有丝毫怠慢,因为它关乎一个个清贫家庭一年的衣食冷暖。麦子养育着农人的生命,也涵泳着村庄的生命。诗人眼中的“一夜南风起,小麦覆陇黄”是一种风景,一种艰辛,更是一种慈悲。
多年后,我已生疏农事,目光也不再澄澈如初,但麦收时节,总会走出郊外寻找乡村,寻找麦子。透过茂密的阴翳,依然感觉得到一波波金色的麦子环绕着村庄,在阳光下灼灼若夭,翩翩起舞。而阴翳间的那条小道,便是通往故乡的路。
麦子多产于北方,我的家乡皖中丘陵每年也种麦子,左近的许多村庄都辟有一块块麦田。麦收时节,骄阳灼灼,麦浪翻滚。
稻子与小麦是家乡种植的两大谷类作物,亦是日常所食之物。稻子分早、晚稻两季,当年种当年收;小麦头年种,第二年收,是谓冬小麦,生长周期比稻子要长得多。
每年九、十月间,地里的棉花、山芋、花生等旱地作物采收后,只等老天眷顾,落一场透秋雨,农人便于土壤里遍施有机肥,将麦垄耙得平整细碎,种麦撒播下地后,方能歇口气。
庄稼人心里装的多为农事,所谓“家中有粮,心中不慌”。麦子播下后,父亲有事无事总会扛一把铁锹,到田岗上走走看看,麦子何时出苗,土壤墒情如何,是否该补种追肥?寒冬腊月,一场大雪铺天盖地,父亲看着窗外,对自己也像对家人道:“冬麦三层被,瑞雪兆丰年哩。”立春以后,几场春雨,麦苗褪去冬装,快速返青,分蘖、拔节、抽穗、扬花、灌浆,小满前后已齐膝着腰饱满茁壮。放学路上,肚子咕噜噜打转,便丢下书包,拔一株麦穗,搓掉麦衣,一把撂进口中,尚未完全成熟的麦穗韧中透绿,嫩的还滋出麦浆。男孩胆大,就地取材架火来烤,焦糊的麦穗香、脆、糙,却并不好吃,倒弄得小脸像鬼画符。晚上,有的直喊肚子痛,有的第二天拉稀时还出现一粒粒麦子,却又不敢告诉大人。
杏黄麦熟,展眼田岗一片金黄,清风送来阵阵麦香。父亲走在麦垄边,看看风向又看看庄稼,捻一穗麦子搓成麦粒摊在掌心,笑了。麦香氤氲村庄的时候,百户千家正磨刀霍霍。这时蛙鸣阵阵,布谷声声,禽鸟的啼鸣成了夏日田园最美丽苦涩的抒情。父亲备好连枷、木锨、箩筐、草叉,铲除场基四周的杂草,拉着磙子压平松土。母亲坐在院子里,“嚯嚯,嚯嚯……”一把一把将镰刀磨得锋利,阳光下闪着耀眼的银光。
父亲并不能整日在田间劳作,他得回药厂指挥生产。母亲只遗憾不能多长出几条手臂。劳力不足,小孩上阵,农业劳动本是田家儿女书本之外的必修功课。不止于我,村里半大孩子亦多半如此。谚语有“麦收九成动手割,莫等熟透颗粒落”。天蒙蒙亮下地,麦穗上还挂着晶亮的露珠;日出三竿,麦田里溽热潮湿,浑身上下火辣辣的。割麦(割稻)先从学打“绕子”开始。打一副绕子,割几把麦子(稻子)置于其上,捆好,拧紧,再继续下一个,循环往复。瓢虫、蚂蚱、小蛾子都飞远点吧,母亲一个上午都没有直一下身子。宽大的草帽下,我的头发紧贴着额头,水洗一般。有一种“牛霸”苍蝇,专叮脊背,那滋味可够人受的。凉鞋滑脱,麦桩戳脚,麦芒搔得脸颊又痒又痛,手掌慢慢磨出一个血泡。
回头,麦茬一片虚白。
乡间路窄,平板车拉不得,全靠肩挑。父亲抽空回来担上几个时辰,母亲既割又挑,插秧时还要犁田打耙。如果空着手,几根遗落在路上的麦穗,母亲便会弯腰捡起。一年夏天,我已很熟练地跟在母亲身边快速挥镰,不料镰刀触到一块瓦砾,锋利的刀刃毫不留情削去我小半截指头,血流一地,母亲骇坏了。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人,没有遭遇锄头镰刀剜破手指脚趾的又有几人?伤指几月后方才痊愈,至今疤痕犹在,我亦从此留下血晕的毛病。
晴热的午后,连枷声急促单调地响着,村里男女老幼几乎都上阵了,场基上尘屑飞扬,连枷声连成一片。再热,也得裹着头巾,穿着长褂长裤,因为麦芒弄到身上浑身刺挠难耐。夜幕降临,打麦场灯火通明,白炽灯四近飞蛾成群,萤火虫在漆黑处一闪一闪。大人们连夜鏖战,脱粒、扬场、翻秸、堆垛,怕突然到来的坏天气,又恐误了农时。欢喜无比的是那些拖着鼻涕的小毛头,场基上捉虫嬉戏,窜来窜去。如此连天带夜要忙好几天,毛头们跟着无厘头地疯闹几日,玩累了,顺势倒在热烘烘的麦秸垛旁。直到麦子扬净晒干,一咬嘎嘣嘎嘣脆,收仓了,农人才心安踏实。
收割后的麦地成了鸟雀们的天堂,偶遇小田鼠倏忽跑过,低头弯腰的拾荒者,背着口袋从这片麦地走向那片麦地。
寂静是暂时的,空旷亦是暂时的,麦地随之被翻耕,抽水车轰隆隆,一夜到天亮转个不停,麦田灌水后重新反过来播插晚稻。路面有些烫脚,水田里的水温热热的。秧苗插下去了,晚风中轻轻摇曳,又一茬新的生命在天地间铺展,经受烈日的炙烤,孕育下一季的成熟与收获。
一茬茬农事令农人不敢有丝毫怠慢,因为它关乎一个个清贫家庭一年的衣食冷暖。麦子养育着农人的生命,也涵泳着村庄的生命。诗人眼中的“一夜南风起,小麦覆陇黄”是一种风景,一种艰辛,更是一种慈悲。
多年后,我已生疏农事,目光也不再澄澈如初,但麦收时节,总会走出郊外寻找乡村,寻找麦子。透过茂密的阴翳,依然感觉得到一波波金色的麦子环绕着村庄,在阳光下灼灼若夭,翩翩起舞。而阴翳间的那条小道,便是通往故乡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