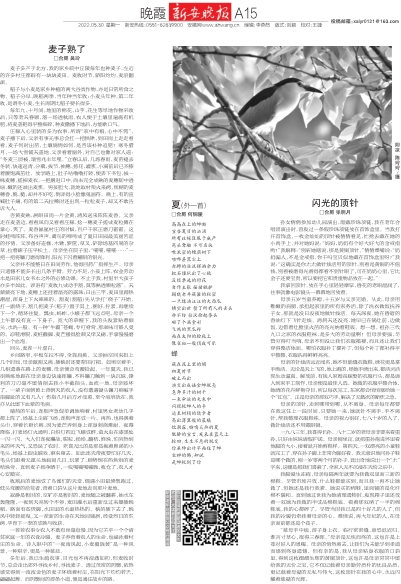发布日期:
闪光的顶针
□合肥张明月
孙女倩倩参加幼儿园演出,需戴珍珠项链,我在老年合唱团演出时,曾发过一条假珍珠项链放在首饰盒里。当我打开首饰盒,一枚金灿灿的顶针被倩倩看见,忙抢去戴在她的小肉手上,并对她妈说:“妈妈,奶奶有个好大好大的金戒指哟!”我解释:“别听她瞎说,那是黄铜顶针。”倩倩犟嘴说:“奶奶骗人,不是金戒指,你干吗宝贝似地藏在首饰盒里呀?”我说:“这确实是你太太做针线活用的顶针,别看是黄铜的不值钱,别看被磨得光滑得都看不到针眼了,可在奶奶心里,它比金子还要宝贵,所以要把它和贵重物品放在一起。”
我拿回顶针,放在手心里轻轻摩挲,昏花的老眼湿润了,往事就像电影镜头一幕幕地回放着。
母亲五岁当童养媳,十五岁与父亲完婚。从此,母亲用稚嫩的肩膀,承担起家里的所有家务活,除了洗衣做饭抚养子女,那就是没日没夜地做针线活。每天深夜,她在昏暗的香油灯下飞针走线。清晨天还没亮,她早已在锅灶前,边做饭,边借着灶膛里火苗的亮光纳着鞋底。想一想,祖孙三代九口之家的衣服鞋袜,是多大的劳动量啊!但母亲要强,尽管穷得叮当响,母亲不但没让我们衣服褴褛,而且还让我们穿得整洁体面。哪怕衣服补丁摞补丁,但每个补丁都补得平平整整,衣服洗得鲜鲜亮亮。
母亲的针线活远近闻名,她不但能缝衣做鞋,绣花更是拿手绝活。无论是天上飞的、地上跑的,经她手绣出来,都活灵活现生动逼真。解放前,有钱人家婚丧嫁娶的衣服行头,都是请人到家手工制作,母亲便是最佳人选。她做的衣服平整合体,她绣的花卉鲜艳夺目,所以每次完工,东家都会悄悄塞给她一个“红包”。正是母亲的那双巧手,解决了无数次的断炊之急。
母亲的顶针,走到哪带到哪,从不离身。母亲每年都要在我这住上一段时间,只要她一来,她就针不离手,手不离针,帮我整理衣服鞋袜。母亲的视力很好,七八十岁的人了,做针线活还不用戴眼镜。
一九八三年,我喜得长孙。八十二岁的老母亲非要来看重孙,只好由妹妹请假护送。母亲刚坐定,就把重孙抱进怀里看他脚的大小,接着就开始剪鞋样。第四天,一双漂亮的小童鞋就完工了,穿在孙子脚上非常合脚好看。我无意识地问孙子鞋是哪个做的,刚一岁零两个月的孙子,竟出奇地说出一个“太”字来,这硬是把我们喜蒙了,全家人无不沉浸在天伦之乐中。
我脚爱生冻疮,母亲每隔两年就要为我做双里面三新的棉鞋。尽管市场开放,什么鞋都能买到,而且我一再不让她做了,但她还是我行我素。她说买的棉鞋,里面铺的是化纤棉不暖和。直到她过世我为她清理遗物时,发现箱子里还放着一双她为我做的半成品棉鞋底。看着那双纳了一半的棉鞋底,我的心都碎了。尽管当时我已是四十好几的人了,但我的冷暖仍牵挂着母亲的心。难怪说,再大年纪的人,在母亲面前都还是个孩子。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母亲是无疾而终的,这也许是上苍对好人的恩赐。母亲的悄然离去,让我们为未能尽到孝道而感到终身遗憾。但有幸的是,我从母亲贴身衣服的口袋里,得到这枚熠熠生辉的黄铜顶针,这也许是母亲冥冥中留给我的无价之宝,它不仅记载着母亲勤劳质朴的优良品质,更记载着母爱的无私与伟大,这枚顶针在我的心中,永远闪耀着慈爱的光辉。
孙女倩倩参加幼儿园演出,需戴珍珠项链,我在老年合唱团演出时,曾发过一条假珍珠项链放在首饰盒里。当我打开首饰盒,一枚金灿灿的顶针被倩倩看见,忙抢去戴在她的小肉手上,并对她妈说:“妈妈,奶奶有个好大好大的金戒指哟!”我解释:“别听她瞎说,那是黄铜顶针。”倩倩犟嘴说:“奶奶骗人,不是金戒指,你干吗宝贝似地藏在首饰盒里呀?”我说:“这确实是你太太做针线活用的顶针,别看是黄铜的不值钱,别看被磨得光滑得都看不到针眼了,可在奶奶心里,它比金子还要宝贵,所以要把它和贵重物品放在一起。”
我拿回顶针,放在手心里轻轻摩挲,昏花的老眼湿润了,往事就像电影镜头一幕幕地回放着。
母亲五岁当童养媳,十五岁与父亲完婚。从此,母亲用稚嫩的肩膀,承担起家里的所有家务活,除了洗衣做饭抚养子女,那就是没日没夜地做针线活。每天深夜,她在昏暗的香油灯下飞针走线。清晨天还没亮,她早已在锅灶前,边做饭,边借着灶膛里火苗的亮光纳着鞋底。想一想,祖孙三代九口之家的衣服鞋袜,是多大的劳动量啊!但母亲要强,尽管穷得叮当响,母亲不但没让我们衣服褴褛,而且还让我们穿得整洁体面。哪怕衣服补丁摞补丁,但每个补丁都补得平平整整,衣服洗得鲜鲜亮亮。
母亲的针线活远近闻名,她不但能缝衣做鞋,绣花更是拿手绝活。无论是天上飞的、地上跑的,经她手绣出来,都活灵活现生动逼真。解放前,有钱人家婚丧嫁娶的衣服行头,都是请人到家手工制作,母亲便是最佳人选。她做的衣服平整合体,她绣的花卉鲜艳夺目,所以每次完工,东家都会悄悄塞给她一个“红包”。正是母亲的那双巧手,解决了无数次的断炊之急。
母亲的顶针,走到哪带到哪,从不离身。母亲每年都要在我这住上一段时间,只要她一来,她就针不离手,手不离针,帮我整理衣服鞋袜。母亲的视力很好,七八十岁的人了,做针线活还不用戴眼镜。
一九八三年,我喜得长孙。八十二岁的老母亲非要来看重孙,只好由妹妹请假护送。母亲刚坐定,就把重孙抱进怀里看他脚的大小,接着就开始剪鞋样。第四天,一双漂亮的小童鞋就完工了,穿在孙子脚上非常合脚好看。我无意识地问孙子鞋是哪个做的,刚一岁零两个月的孙子,竟出奇地说出一个“太”字来,这硬是把我们喜蒙了,全家人无不沉浸在天伦之乐中。
我脚爱生冻疮,母亲每隔两年就要为我做双里面三新的棉鞋。尽管市场开放,什么鞋都能买到,而且我一再不让她做了,但她还是我行我素。她说买的棉鞋,里面铺的是化纤棉不暖和。直到她过世我为她清理遗物时,发现箱子里还放着一双她为我做的半成品棉鞋底。看着那双纳了一半的棉鞋底,我的心都碎了。尽管当时我已是四十好几的人了,但我的冷暖仍牵挂着母亲的心。难怪说,再大年纪的人,在母亲面前都还是个孩子。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母亲是无疾而终的,这也许是上苍对好人的恩赐。母亲的悄然离去,让我们为未能尽到孝道而感到终身遗憾。但有幸的是,我从母亲贴身衣服的口袋里,得到这枚熠熠生辉的黄铜顶针,这也许是母亲冥冥中留给我的无价之宝,它不仅记载着母亲勤劳质朴的优良品质,更记载着母爱的无私与伟大,这枚顶针在我的心中,永远闪耀着慈爱的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