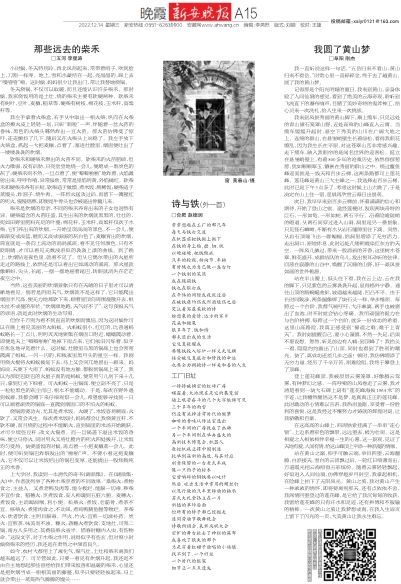发布日期:
那些远去的柴禾
□五河李星涛
小时候,冬天特别冷,西北风刮起来,常带着哨子,吹到脸上,刀割一样疼。地上,雪和水凝结在一起,亮晶晶的,踩上去“嘎喳喳”响。这时候,妈妈很少让我出门,常让我替她烧锅。
冬天烧锅,不仅可以取暖,而且还能认识许多柴禾。那时候,我家烧饭用的是土灶,烧的柴禾主要有软硬两种。软柴禾有树叶、豆叶、麦穰、稻草等,硬柴有树枝、棉花枝、玉米秆、高粱秆等。
我左手拿着火柴盒,右手从中取出一根火柴,纵向在火柴盒的擦火皮上轻轻一划,只听“刺啦”一声,伴随着一丝火药的香味,黑色的火柴头蓦然炸出一豆火苗。那火苗仿佛受了惊吓,连连颤抖了几下,随后又在火柴头上站稳了。我左手放下火柴盒,抓起一大把麦穰,点着了,塞进灶膛里,烟囱便吐出了一缕缕袅袅的炊烟。
软柴禾和硬柴禾燃出的火苗不同。软柴禾的火苗肥硕,但火力微弱,没有后劲,只亮堂堂地烧一会儿,便熄成一堆炭色的灰了;硬柴禾则不然,一旦点着了,便“噼噼啪啪”地炸着,火焰激射出来,呼呼作响,异常强劲,常常是里焰明黄,外焰橘红。软柴禾和硬柴禾各有长短,软柴适于做馍,煮米饭,熬稀饭;硬柴适于蒸馒头,炸圆子,烧牛肉。一阵烈火猛攻过后,再留下一篝猩红的死火,慢慢焐熬,即便是牛骨头也会被逼出骨髓儿来。
柴禾是炊烟的母亲,不同的柴禾养育出来的子女也迥然有异。硬柴蕴含的火苗旺盛,其生出来的炊烟就黑黑的,壮壮的,宛如田野里肥料充足的叶蔓;棉花秆、玉米秆、高粱秆仅次于木柴,它们养出来的炊烟,一开始呈现淡淡的黑色,不一会儿,便渐渐变成浅蓝,继而又淡成弱弱的灰白色了;麦穰育出的炊烟,简直就是一条向上流动的涓涓溪流,看不见任何颜色,只有不眨眼睛,才可以看见无数波浪似的袅袅上漾的曲线。到了晚上,炊烟钻进夜色里,就看不见了。但从它偶尔带出的火星所走过的路线上,依然还是可以看出它如涌动的溪流。那火星就像蝌蚪,尖头,长尾,一摆一摆地摇着尾巴,转眼就消失在茫茫夜空之中。
当然,这些美丽的炊烟景象只有在天晴的日子里才可以清晰地看见。倘若是阴雨天气,炊烟就不是这样了,它只能爬出烟囱半尺高,便无力地蔫软下来,顺着屋顶向周围漫散开去,根本扯不成蔓的形状。“炊烟顺地跑,天气好不了”,这句预报天气的谚语,就是此时炊烟的生动写照。
但你千万别为看不到直直的炊烟而懊恼,因为这时候你可以在晚上看见美丽的火蚂蚁。火蚂蚁很小,红红的,比普通蚂蚁略长一丁点儿,明明灭灭地聚集在烟囱口附近,蠕蠕爬动着,即便是天上“噼噼啪啪”地掉下雨点来,它们依旧闪烁着,似乎在焦急地寻觅着什么。这时候,灶膛里乌黑的锅底上也会密密爬满了蚂蚁,一闪一闪的,和秋夜里黑月头的星空一样。我刚用烧火棍将火蚂蚁拨划下去,马上又会突兀地冒出一群来。妈妈说,天要下大雨了,蚂蚁没有地方躲,都躲到锅底上来了。我以为那眨巴眨巴的火星子真的是蚂蚁,便常用勺儿刮下来十几只,拿到灯光下细看。可火蚂蚁一出锅底,便立刻不亮了,只是一粒粒黑色的灰尘而已,根本不能蠕动。于是,每次在野外遇到蚁群,我都会蹲下来仔细观察一会儿,希望能够寻找到一只可以顺着滚烫的锅底一直爬到烟囱口的不怕火的蚂蚁。
烧锅需要功夫,尤其是煮米饭。火硬了,米饭容易糊底;火软了,又常会夹生。每次煮米饭时,妈妈都会让我烧黄豆秆,不软不硬,而且烧的过程中不能断火,直到锅里的米汤开始跳跃,才可少续些豆秆,改文火慢煮。而一旦锅盖下溢出米饭的香味,便立马停火,同时用火叉将灶膛内的死火四处拨开,让米饭均匀受热。快要盛饭的时候,再点着一小把麦穰蒸一会儿。此时,便可听到锅巴炸裂发出的“啪啪”声。不要小看这把麦穰火,它不仅可以让米饭结出的锅巴变厚,还能提出一股焦脆纯正的米香。
上大学时,我读到一本清代的奇书《调鼎集》。在《调鼎集·火》中,作者就列举了各种木柴烹煮的不同效果:“桑柴火:煮物食之,主益人。又煮老鸭及肉等,能令极烂,能解一切毒,秽柴不宜作食。稻穗火:烹煮饭食,安人神魂到五脏六腑。麦穗火:煮饭食,主消渴润喉,利小便。松柴火:煮饭,壮筋骨,煮茶不宜。栎柴火:煮猪肉食之,不动风,煮鸡鸭鹅鱼腥等物烂。茅柴火:炊者饮食,主明目解毒。芦火、竹火:宜煎一切滋补药。炭火:宜煎茶,味美而不浊。糠火:砻糠火煮饮食,支地灶,可架二锅,南方人多用之,其费较柴火省半。惜春时糠内入虫,有伤物命。”这段文字,对于木柴之作用,说得似乎有些玄,但对照小时候烧柴禾的经历,我还是在肃然之中颔首良久。
如今,农村大都用上了液化气、煤气灶,土灶和柴禾离我们越来越远了。可尽管如此,只要一看见有炊烟升起,我还是不由自主地想起那些曾经给我们带来饭香和温暖的柴禾,心里还是把炊烟当成一根根美丽的藤蔓,似乎只要轻轻拔起来,马上就会带出一蒸笼热气腾腾的馒头……
小时候,冬天特别冷,西北风刮起来,常带着哨子,吹到脸上,刀割一样疼。地上,雪和水凝结在一起,亮晶晶的,踩上去“嘎喳喳”响。这时候,妈妈很少让我出门,常让我替她烧锅。
冬天烧锅,不仅可以取暖,而且还能认识许多柴禾。那时候,我家烧饭用的是土灶,烧的柴禾主要有软硬两种。软柴禾有树叶、豆叶、麦穰、稻草等,硬柴有树枝、棉花枝、玉米秆、高粱秆等。
我左手拿着火柴盒,右手从中取出一根火柴,纵向在火柴盒的擦火皮上轻轻一划,只听“刺啦”一声,伴随着一丝火药的香味,黑色的火柴头蓦然炸出一豆火苗。那火苗仿佛受了惊吓,连连颤抖了几下,随后又在火柴头上站稳了。我左手放下火柴盒,抓起一大把麦穰,点着了,塞进灶膛里,烟囱便吐出了一缕缕袅袅的炊烟。
软柴禾和硬柴禾燃出的火苗不同。软柴禾的火苗肥硕,但火力微弱,没有后劲,只亮堂堂地烧一会儿,便熄成一堆炭色的灰了;硬柴禾则不然,一旦点着了,便“噼噼啪啪”地炸着,火焰激射出来,呼呼作响,异常强劲,常常是里焰明黄,外焰橘红。软柴禾和硬柴禾各有长短,软柴适于做馍,煮米饭,熬稀饭;硬柴适于蒸馒头,炸圆子,烧牛肉。一阵烈火猛攻过后,再留下一篝猩红的死火,慢慢焐熬,即便是牛骨头也会被逼出骨髓儿来。
柴禾是炊烟的母亲,不同的柴禾养育出来的子女也迥然有异。硬柴蕴含的火苗旺盛,其生出来的炊烟就黑黑的,壮壮的,宛如田野里肥料充足的叶蔓;棉花秆、玉米秆、高粱秆仅次于木柴,它们养出来的炊烟,一开始呈现淡淡的黑色,不一会儿,便渐渐变成浅蓝,继而又淡成弱弱的灰白色了;麦穰育出的炊烟,简直就是一条向上流动的涓涓溪流,看不见任何颜色,只有不眨眼睛,才可以看见无数波浪似的袅袅上漾的曲线。到了晚上,炊烟钻进夜色里,就看不见了。但从它偶尔带出的火星所走过的路线上,依然还是可以看出它如涌动的溪流。那火星就像蝌蚪,尖头,长尾,一摆一摆地摇着尾巴,转眼就消失在茫茫夜空之中。
当然,这些美丽的炊烟景象只有在天晴的日子里才可以清晰地看见。倘若是阴雨天气,炊烟就不是这样了,它只能爬出烟囱半尺高,便无力地蔫软下来,顺着屋顶向周围漫散开去,根本扯不成蔓的形状。“炊烟顺地跑,天气好不了”,这句预报天气的谚语,就是此时炊烟的生动写照。
但你千万别为看不到直直的炊烟而懊恼,因为这时候你可以在晚上看见美丽的火蚂蚁。火蚂蚁很小,红红的,比普通蚂蚁略长一丁点儿,明明灭灭地聚集在烟囱口附近,蠕蠕爬动着,即便是天上“噼噼啪啪”地掉下雨点来,它们依旧闪烁着,似乎在焦急地寻觅着什么。这时候,灶膛里乌黑的锅底上也会密密爬满了蚂蚁,一闪一闪的,和秋夜里黑月头的星空一样。我刚用烧火棍将火蚂蚁拨划下去,马上又会突兀地冒出一群来。妈妈说,天要下大雨了,蚂蚁没有地方躲,都躲到锅底上来了。我以为那眨巴眨巴的火星子真的是蚂蚁,便常用勺儿刮下来十几只,拿到灯光下细看。可火蚂蚁一出锅底,便立刻不亮了,只是一粒粒黑色的灰尘而已,根本不能蠕动。于是,每次在野外遇到蚁群,我都会蹲下来仔细观察一会儿,希望能够寻找到一只可以顺着滚烫的锅底一直爬到烟囱口的不怕火的蚂蚁。
烧锅需要功夫,尤其是煮米饭。火硬了,米饭容易糊底;火软了,又常会夹生。每次煮米饭时,妈妈都会让我烧黄豆秆,不软不硬,而且烧的过程中不能断火,直到锅里的米汤开始跳跃,才可少续些豆秆,改文火慢煮。而一旦锅盖下溢出米饭的香味,便立马停火,同时用火叉将灶膛内的死火四处拨开,让米饭均匀受热。快要盛饭的时候,再点着一小把麦穰蒸一会儿。此时,便可听到锅巴炸裂发出的“啪啪”声。不要小看这把麦穰火,它不仅可以让米饭结出的锅巴变厚,还能提出一股焦脆纯正的米香。
上大学时,我读到一本清代的奇书《调鼎集》。在《调鼎集·火》中,作者就列举了各种木柴烹煮的不同效果:“桑柴火:煮物食之,主益人。又煮老鸭及肉等,能令极烂,能解一切毒,秽柴不宜作食。稻穗火:烹煮饭食,安人神魂到五脏六腑。麦穗火:煮饭食,主消渴润喉,利小便。松柴火:煮饭,壮筋骨,煮茶不宜。栎柴火:煮猪肉食之,不动风,煮鸡鸭鹅鱼腥等物烂。茅柴火:炊者饮食,主明目解毒。芦火、竹火:宜煎一切滋补药。炭火:宜煎茶,味美而不浊。糠火:砻糠火煮饮食,支地灶,可架二锅,南方人多用之,其费较柴火省半。惜春时糠内入虫,有伤物命。”这段文字,对于木柴之作用,说得似乎有些玄,但对照小时候烧柴禾的经历,我还是在肃然之中颔首良久。
如今,农村大都用上了液化气、煤气灶,土灶和柴禾离我们越来越远了。可尽管如此,只要一看见有炊烟升起,我还是不由自主地想起那些曾经给我们带来饭香和温暖的柴禾,心里还是把炊烟当成一根根美丽的藤蔓,似乎只要轻轻拔起来,马上就会带出一蒸笼热气腾腾的馒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