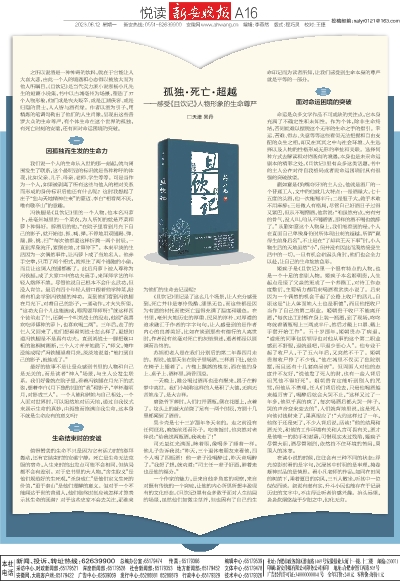发布日期:
孤独·死亡·超越
□天津 吴丹
之所以说酒是一种神奇的饮料,就在于它能让人大喜大悲,由此一个人的境遇和心态得以被放大而为他人所瞩目。《且饮记》是当代实力派小说家杨小凡先生的短篇小说集,书中以古城亳州为场景,塑造了37个人物形象,他们或是农夫贩卒、或是江湖侠客、或是归隐的贤士,人人皆与酒有缘。作者以酒为引子,用精炼的笔调勾勒出了他们的人生肖像,呈现出这些普罗大众的生命尊严,有个体生命在这个世界的孤独,有死亡时刻的安谧,还有面对命运困境的突破。
一
因孤独而生发的生命力
我们说一个人的生命从入世的那一刻起,就与周围发生了联系,这个最明显的标识就是各种称呼的体现,比如父亲、儿子、母亲、老师、学生等等。可是当作为一个人,如果被剥离了所有这些与他人的相对关系而形成的身份标识后他还有什么呢?这时我想起了庄子“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豪迈、李白“相看两不厌,唯有敬亭山”的意趣。
冯铁腿是《且饮记》里的一个人物,他本名冯萝卜,是亳州城里的一个菜农,为人所知的就是芹菜和萝卜种得好。醉酒后的他,“在院子里看到月光下自己的影子,就开始追、抓、喊、撵,不停地用双腿踢、弹、踹、跺、挑、扫”“每次他都要这样折腾一两个时辰,一直到浑身流汗,累倒在地,才算停下”。本来平淡的生活因为一次偶然事件,让冯萝卜成了当地名人。他赤手空拳,只用了两个招式,就抓住了两个逃跑的小偷,而且让这俩人的腿都断了。此后冯萝卜被人尊称为冯铁腿,成了大家口中的功夫高手,来拜师学艺的年轻人络绎不绝。尽管他说自己根本不会什么武功,但没人肯信。最后有四个年轻人借口跟着他学种菜,盼着有机会学到冯铁腿的神功。直到他们看到冯铁腿在月光下,对着自己的影子,一通动作,才大失所望,“这功夫自个儿也能练成,哪需要拜师呀!”就这样四个徒弟走了仨,还剩一个叫刘战士的没走,他说“我喜欢吃师傅种的萝卜,也喜欢喝二两”。三年后,走了的仨人又回来了,他们想看看刘战士怎么样了,更想知道冯铁腿是不是真有功夫。直到刘战士一脚把碗口粗的泡桐树踢断,三个人才齐齐地跪下,“师父,俺咋没练成呢?”冯铁腿望着月亮,淡淡地说道:“能打到自己的影子,就练成了。”
最好的故事不是让受众感到书里的人物和自己是无关的,而是读者“神入”场景,与主人公发生联系。我们好像就在院子里,看着冯铁腿在月光下的武姿,想着李白《月下独酌》里的“我”和影子,“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一个人能和谐地与自己相处,一个人面对世界时,可以坦然地对话天地,通过自我仪式来展示生命的真妙,由孤独而饱满自我生命,这本身不就是生命应有的意义吗?
二
生命结束时的安谧
值得赞美的生命不只是因为它有活力时的澎拜轰动,还有它结束时的安谧宁静。死亡是生命无法克服的宿命,人生来时的出发点可能不会相同,但结局都不会有差别。对于史书里的大人物,“舍生取义”是他们规范好的生死观,“杀身成仁”是他们定义生死的价值,“重于泰山”是他们理解的意义。但对于一个不能闻达于世的普通人,他们临终时刻应该怎样才算表示其生命的圆满?对于这些史家不会去关注,那谁来为他们的生命去记录呢?
《且饮记》里记录了这么几个场景,让人充分感受到,死亡并非是寒冷残酷、漆黑无色,而这些都是因为有酒的衬托而使死亡显得充满了温度和暖色。在书里,亳州大地历史的厚重、民风的淳朴、对厚道的追求融汇于作者的字字句句,让人感受到的是作者内心的良善美好,比如在谈到那些有德行的人离世时,作者没有丝毫对死亡的灰暗描述,逝者都是以圆满而告终的。
苏旭初老人是在我们分别后的第二年春四月走的。据说,他那天坐在院子里喝酒,三杯酒下肚,就坐在椅子上睡着了。古槐上飘落的槐花,洒在他的身上、桌子上、酒杯里,清香四溢。
一天晚上,雕公喝过酒再也没有醒来,属于在醉梦中离世。我们小城称这样的人是积了大德,无病无苦地走了,是大吉祥。
磨瓷爷下葬时,人们打开酒瓶,倒在花圈上,点着了。坟头上的蓝火苗烧了足有一两个时辰,方圆十几里都闻到了酒香。
吴卡壳是七十三岁那年冬天老的。走之前没有任何征兆,晚饭前还看孙子。吃晚饭时,他突然对老伴说:“给我找两瓶酒,我该走了!”
司无量红光满面,眯着眼,像喝多了睡着一样。他儿子告诉我说:“昨天,三个退休老朋友来看他,四个人喝了四瓶酒!他一辈子没喝醉过,昨天竟喝醉了。”我想了想,就劝道:“司主任一辈子好酒,醉着走也是他的福分。”
一个作家的魅力,是来自他多角度的观察,来自对既有传统的一个突破,让他的内心所思所想丰盈现有的文化形态。《且饮记》里有众多敢于面对人生结局的场景,虽然他们如微尘草芥,但也因有了自己的生命印记而为读者所知,让我们感受到生命本身的尊严就是平等的一部分。
三
面对命运困境的突破
命运是众多文学作品不可或缺的关注点,它本身充满了不确定性和未知性。作为个体,除非生命终结,否则就难以摆脱这个无形的生命之手的指引。幸运、苦难、得志、失意等等这些看似无法把握和自由支配的众生之相,却又在冥冥之中与社会环境、人生选择以及人物的性格形成无形的牵扯和关联。选择何种方式去解读和对待既有的境遇,本身也是未来命运剧本的精彩之处。《且饮记》里有众多这类话题,书中的主人公在对待自我格局或者说命运困境时具有很强的突破欲望。
蒯如意是《狗嘴夺牙》的主人公,他就是酒厂的一个普通工人,文中的他就几大特点:一是酒量大,七十五度的头酒,他一次能喝半斤;二是胆子大,做手术敢不用麻醉;三是做人有格局,尽管自己好酒日子过得又紧巴,但从不喝蹭酒,他常说:“咱虽然穷点,穷有穷的骨气,没人叫,咱从不喝蹭酒,那样的酒不喝也就醉了。”从蒯如意这个人物身上,我们能看到的是,个人在直面自己卑微身份时所体现出来的超越,所谓“赢得生前身后名”,不止是在“了却君王天下事”时,小人物生活的天地虽然“小”,但并没有因此而漠然接受生活中的一切,一旦有机会崭露头角时,他们也会全力以赴,让自己的生命绽放色彩。
姬疯子是《且饮记》里一个很有特点的人物,也是一个十足的悲剧人物。姬疯子本名姬朝贵,人生起点是接了父亲的班成了一个养路工,对待工作态度敷衍,主要精力都用来喝酒看武侠小说了。后来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干起了公路上收尸的活儿,自诩这是“让人体面地入土也是积德”,而且他把收尸当作了自己的第二职业。姬朝贵干收尸不能离开酒,“每次出工时都在身上装一瓶酒,到了现场,咚咚咚就着酒瓶喝上三两或半斤,然后才戴上口罩、戴上手套开始工作”。五十岁那年,姬朝贵办了病退,“道班的同事包括领导也对他从事的这个第二职业感到不舒服,退就退吧,早退少恶心人”。他专业干起了收尸人,干了五六年后,又突然不干了。姬朝贵靠收尸挣了不少钱,“他在城里不仅买了独院别墅,而且还有十几套商品房”。但周围人对他的态度并不友好,“说他发了死人的财,也有一些人背后诅咒他不得好死”。姬朝贵肯定能听到别人的咒骂,但他从不搭理,任人们背后说去,只是他喝酒越来越厉害了,喝醉后就会大哭不止,“这样又过了一年多,他似乎真的疯了,每次喝酒后都大哭一阵子,哭的声音变来变去的”,人们就背地里说,这是死人向他讨钱财来了,果真报应了!“大约这样过了一年,他终于还是死了,不少人背后说,活该!”他的结局和酒无关,和他的工作环境有关和人言可畏有关,酒才是他唯一的助手和慰藉,可惜现实太过残酷,姬疯子尽管大胆,酒尽管刚烈,依然挡不住环境的苦闷,周围人的冰寒。
在读小说的时候,往往会有三种不同的状态:浮光掠影时看的是字句,沉浸其中时明的是事理,掩卷凝神时品的是情思。看小凡老师的作品,如同在田间的树荫下,乘着夏日的凉风,三五人散坐,听其中一位侃侃而谈。叙说有虚有实,升斗小民也能存在于记录历史的文字中,不由得让听者倍感兴趣。抬头远望,袅袅炊烟悠哉于夕阳之中,幻化无穷。
之所以说酒是一种神奇的饮料,就在于它能让人大喜大悲,由此一个人的境遇和心态得以被放大而为他人所瞩目。《且饮记》是当代实力派小说家杨小凡先生的短篇小说集,书中以古城亳州为场景,塑造了37个人物形象,他们或是农夫贩卒、或是江湖侠客、或是归隐的贤士,人人皆与酒有缘。作者以酒为引子,用精炼的笔调勾勒出了他们的人生肖像,呈现出这些普罗大众的生命尊严,有个体生命在这个世界的孤独,有死亡时刻的安谧,还有面对命运困境的突破。
一
因孤独而生发的生命力
我们说一个人的生命从入世的那一刻起,就与周围发生了联系,这个最明显的标识就是各种称呼的体现,比如父亲、儿子、母亲、老师、学生等等。可是当作为一个人,如果被剥离了所有这些与他人的相对关系而形成的身份标识后他还有什么呢?这时我想起了庄子“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豪迈、李白“相看两不厌,唯有敬亭山”的意趣。
冯铁腿是《且饮记》里的一个人物,他本名冯萝卜,是亳州城里的一个菜农,为人所知的就是芹菜和萝卜种得好。醉酒后的他,“在院子里看到月光下自己的影子,就开始追、抓、喊、撵,不停地用双腿踢、弹、踹、跺、挑、扫”“每次他都要这样折腾一两个时辰,一直到浑身流汗,累倒在地,才算停下”。本来平淡的生活因为一次偶然事件,让冯萝卜成了当地名人。他赤手空拳,只用了两个招式,就抓住了两个逃跑的小偷,而且让这俩人的腿都断了。此后冯萝卜被人尊称为冯铁腿,成了大家口中的功夫高手,来拜师学艺的年轻人络绎不绝。尽管他说自己根本不会什么武功,但没人肯信。最后有四个年轻人借口跟着他学种菜,盼着有机会学到冯铁腿的神功。直到他们看到冯铁腿在月光下,对着自己的影子,一通动作,才大失所望,“这功夫自个儿也能练成,哪需要拜师呀!”就这样四个徒弟走了仨,还剩一个叫刘战士的没走,他说“我喜欢吃师傅种的萝卜,也喜欢喝二两”。三年后,走了的仨人又回来了,他们想看看刘战士怎么样了,更想知道冯铁腿是不是真有功夫。直到刘战士一脚把碗口粗的泡桐树踢断,三个人才齐齐地跪下,“师父,俺咋没练成呢?”冯铁腿望着月亮,淡淡地说道:“能打到自己的影子,就练成了。”
最好的故事不是让受众感到书里的人物和自己是无关的,而是读者“神入”场景,与主人公发生联系。我们好像就在院子里,看着冯铁腿在月光下的武姿,想着李白《月下独酌》里的“我”和影子,“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一个人能和谐地与自己相处,一个人面对世界时,可以坦然地对话天地,通过自我仪式来展示生命的真妙,由孤独而饱满自我生命,这本身不就是生命应有的意义吗?
二
生命结束时的安谧
值得赞美的生命不只是因为它有活力时的澎拜轰动,还有它结束时的安谧宁静。死亡是生命无法克服的宿命,人生来时的出发点可能不会相同,但结局都不会有差别。对于史书里的大人物,“舍生取义”是他们规范好的生死观,“杀身成仁”是他们定义生死的价值,“重于泰山”是他们理解的意义。但对于一个不能闻达于世的普通人,他们临终时刻应该怎样才算表示其生命的圆满?对于这些史家不会去关注,那谁来为他们的生命去记录呢?
《且饮记》里记录了这么几个场景,让人充分感受到,死亡并非是寒冷残酷、漆黑无色,而这些都是因为有酒的衬托而使死亡显得充满了温度和暖色。在书里,亳州大地历史的厚重、民风的淳朴、对厚道的追求融汇于作者的字字句句,让人感受到的是作者内心的良善美好,比如在谈到那些有德行的人离世时,作者没有丝毫对死亡的灰暗描述,逝者都是以圆满而告终的。
苏旭初老人是在我们分别后的第二年春四月走的。据说,他那天坐在院子里喝酒,三杯酒下肚,就坐在椅子上睡着了。古槐上飘落的槐花,洒在他的身上、桌子上、酒杯里,清香四溢。
一天晚上,雕公喝过酒再也没有醒来,属于在醉梦中离世。我们小城称这样的人是积了大德,无病无苦地走了,是大吉祥。
磨瓷爷下葬时,人们打开酒瓶,倒在花圈上,点着了。坟头上的蓝火苗烧了足有一两个时辰,方圆十几里都闻到了酒香。
吴卡壳是七十三岁那年冬天老的。走之前没有任何征兆,晚饭前还看孙子。吃晚饭时,他突然对老伴说:“给我找两瓶酒,我该走了!”
司无量红光满面,眯着眼,像喝多了睡着一样。他儿子告诉我说:“昨天,三个退休老朋友来看他,四个人喝了四瓶酒!他一辈子没喝醉过,昨天竟喝醉了。”我想了想,就劝道:“司主任一辈子好酒,醉着走也是他的福分。”
一个作家的魅力,是来自他多角度的观察,来自对既有传统的一个突破,让他的内心所思所想丰盈现有的文化形态。《且饮记》里有众多敢于面对人生结局的场景,虽然他们如微尘草芥,但也因有了自己的生命印记而为读者所知,让我们感受到生命本身的尊严就是平等的一部分。
三
面对命运困境的突破
命运是众多文学作品不可或缺的关注点,它本身充满了不确定性和未知性。作为个体,除非生命终结,否则就难以摆脱这个无形的生命之手的指引。幸运、苦难、得志、失意等等这些看似无法把握和自由支配的众生之相,却又在冥冥之中与社会环境、人生选择以及人物的性格形成无形的牵扯和关联。选择何种方式去解读和对待既有的境遇,本身也是未来命运剧本的精彩之处。《且饮记》里有众多这类话题,书中的主人公在对待自我格局或者说命运困境时具有很强的突破欲望。
蒯如意是《狗嘴夺牙》的主人公,他就是酒厂的一个普通工人,文中的他就几大特点:一是酒量大,七十五度的头酒,他一次能喝半斤;二是胆子大,做手术敢不用麻醉;三是做人有格局,尽管自己好酒日子过得又紧巴,但从不喝蹭酒,他常说:“咱虽然穷点,穷有穷的骨气,没人叫,咱从不喝蹭酒,那样的酒不喝也就醉了。”从蒯如意这个人物身上,我们能看到的是,个人在直面自己卑微身份时所体现出来的超越,所谓“赢得生前身后名”,不止是在“了却君王天下事”时,小人物生活的天地虽然“小”,但并没有因此而漠然接受生活中的一切,一旦有机会崭露头角时,他们也会全力以赴,让自己的生命绽放色彩。
姬疯子是《且饮记》里一个很有特点的人物,也是一个十足的悲剧人物。姬疯子本名姬朝贵,人生起点是接了父亲的班成了一个养路工,对待工作态度敷衍,主要精力都用来喝酒看武侠小说了。后来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干起了公路上收尸的活儿,自诩这是“让人体面地入土也是积德”,而且他把收尸当作了自己的第二职业。姬朝贵干收尸不能离开酒,“每次出工时都在身上装一瓶酒,到了现场,咚咚咚就着酒瓶喝上三两或半斤,然后才戴上口罩、戴上手套开始工作”。五十岁那年,姬朝贵办了病退,“道班的同事包括领导也对他从事的这个第二职业感到不舒服,退就退吧,早退少恶心人”。他专业干起了收尸人,干了五六年后,又突然不干了。姬朝贵靠收尸挣了不少钱,“他在城里不仅买了独院别墅,而且还有十几套商品房”。但周围人对他的态度并不友好,“说他发了死人的财,也有一些人背后诅咒他不得好死”。姬朝贵肯定能听到别人的咒骂,但他从不搭理,任人们背后说去,只是他喝酒越来越厉害了,喝醉后就会大哭不止,“这样又过了一年多,他似乎真的疯了,每次喝酒后都大哭一阵子,哭的声音变来变去的”,人们就背地里说,这是死人向他讨钱财来了,果真报应了!“大约这样过了一年,他终于还是死了,不少人背后说,活该!”他的结局和酒无关,和他的工作环境有关和人言可畏有关,酒才是他唯一的助手和慰藉,可惜现实太过残酷,姬疯子尽管大胆,酒尽管刚烈,依然挡不住环境的苦闷,周围人的冰寒。
在读小说的时候,往往会有三种不同的状态:浮光掠影时看的是字句,沉浸其中时明的是事理,掩卷凝神时品的是情思。看小凡老师的作品,如同在田间的树荫下,乘着夏日的凉风,三五人散坐,听其中一位侃侃而谈。叙说有虚有实,升斗小民也能存在于记录历史的文字中,不由得让听者倍感兴趣。抬头远望,袅袅炊烟悠哉于夕阳之中,幻化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