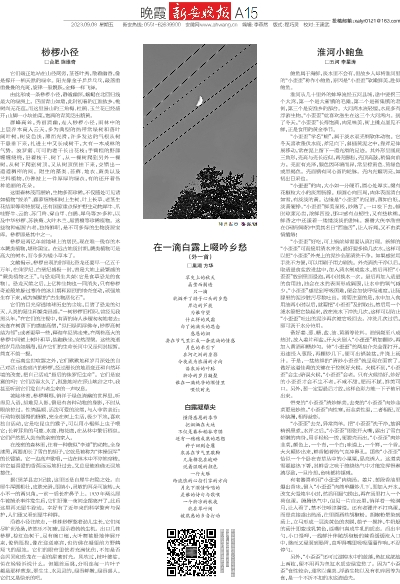发布日期:
桫椤小径
它们端正地站在山径两旁,茎苍叶秀,散着幽香,像是撑开一柄天然的绿伞。阳光像金子乒乒乓乓,敲落重重叠叠的光斑,旋律一般跳跃,金蜂一样飞舞。
由此形成一条桫椤小径,静谧幽深,蜿蜒在北回归线最大的绿洲上。四面青山如黛,此时初春的江淮故乡,桃树尚无花苞,而这里漫山的三角梅、杜鹃、玉兰花已经盛开;山脚一小块油菜,饱满的青荚泛出鹅黄。
群峰高耸,秀丽清幽,走入桫椤小径,雨林中的上层乔木高入云天,多为典型的热带常绿树和落叶阔叶树,树皮色浅,薄而光滑,许多发达的气根从树干悬垂下来,扎进土中又长成树干,大有一木成林的气势。波罗蜜、可可的老干长出花枝;手臂粗的野藤缠缠绕绕,沿着枝干、树丫,从一棵树爬到另外一棵树,从树下爬到树顶,又从树顶倒挂下来,交错出一道道稠密的网。附生的藻类、苔藓、地衣、蕨类以及兰科植物,仿佛披上一件厚厚的绿衣,有的还开着各种艳丽的花朵。
这里森林茂而原始,生物多而珍稀,不仅随处可见诸如植物“绞杀”、藤萝缠绕和树上生树、叶上长草、老茎生花结果等奇特景观,还有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犀牛、爪哇野牛、云豹、苏门羚、穿山甲、白鹂、犀鸟等20多种,以及中华桫椤、苏铁蕨、大叶木兰、黑黄檀等珍稀植物。这些物种起源古老,独特鲜明,是不可多得的生物资源宝库。桫椤即是其中之一。
桫椤是两亿年前地球上的居民,现在唯一残存的木本蕨类植物,堪称国宝。在远古地质时期,蕨类植物可是高大的树木,而今多为矮小草本了。
文献揭示,桫椤出现的时间比恐龙还要早一亿五千万年,在侏罗纪、白垩纪盛极一时,曾是大地上最繁盛的“蕨类植物之王”,与恐龙同生共荣(它是食草恐龙的食物)。恐龙灭绝之后,上亿种生物也一同消失,只有桫椤奇迹般地躲过寒冷的冰川期和剧烈的地壳变动,顽强地生存下来,成为缄默的“古生物活化石”。
它们的目光穿透地球历史的尘埃,目睹了恐龙的幻灭、人类的诞生和繁荣昌盛。“一树桫椤旧相识,曾经见我黑头年。”在它们的注视中,有清的诗人步履匆匆地老去;流连在树荫下的盛唐高僧,“拟扫绿阴浮佛寺,桫椤高树结为邻”;或者更早一些,释迦牟尼佛走来,在两株高大的桫椤中间铺上树叶和草,结跏趺坐,安然涅槃。这些流逝的岁月浩如烟海,但在它们的生命长河中又是何其短暂,简直不值一提。
在远离尘世喧嚣之外,它们默默地和岁月深处的自己对话:这些高古的桫椤,经过漫长的地质变迁和自然环境的改变,把自己活成“最后的侏罗纪生命”。它们是寂寞的吗?它们活得太久了,孤独地站在深山峡谷之中,我甚至听到它们发自古老生命的一声叹息。
坡陡林密,桫椤婀娜,徜徉于绿色清幽的世界里,听得见人语,却难见人影,倒是有各种动物的身影,不时从眼前掠过。性情温顺、活泼可爱的浣熊,与人非常亲近;行动特别缓慢的蜂猴,完全在树上生活,极少下地,喜欢独自活动,它是吃昆虫的猴子,可以用小棍绑上虫子喂它;长着茸角的马鹿、水鹿、梅花鹿,在丛林中繁衍栖息,它们俨然把人类当做亲密的家人。
在茂密的森林里,住着一种貌似“李逵”的动物,全身漆黑,两腮却长了雪白的胡子,它就是被称为“体操冠军”的长臂猿。它一边高声歌唱,一边在林木中不停地穿梭,将它最喜爱的香蕉远远地扔过去,又总是能准确无误地接住。
据《思茅县志》记载,这里还是白犀牛归隐之处。白犀牛浑圆粗壮,皮肤光滑,眼睛小,灵敏的耳朵可旋转,大小不一的两只角,一前一后长在鼻子上。1933年两头犀牛被捕杀事件发生后,它们好像一夜间全部离开了,此后这里再无犀牛踪迹。幸好有了近年来的科学繁育与保护,人们重又看到犀牛种群。
沿着小径往前走,一株株桫椤憋着劲儿生长,它们阅尽旷世沧桑,依然乐不知疲,显示着勃勃生机。出口几株桫椤,棕红色树干,足有碗口粗,大叶舞袖般地伸展开来,俊俏挺拔,像在迎送嘉宾,也仿佛在凝望前方野鹤翔飞的湿地。它们的眼帘里恍若充满忧伤,不知是否会闪回和恐龙在一起的甜蜜时光。风吹过,枝叶婆娑,似在轻轻诉说什么。但翘首远眺,分明连每一片叶子都是那样葱茏,翠生生、水灵灵的,绿得鲜嫩,绿得喜人,它们又是快乐的吧。
由此形成一条桫椤小径,静谧幽深,蜿蜒在北回归线最大的绿洲上。四面青山如黛,此时初春的江淮故乡,桃树尚无花苞,而这里漫山的三角梅、杜鹃、玉兰花已经盛开;山脚一小块油菜,饱满的青荚泛出鹅黄。
群峰高耸,秀丽清幽,走入桫椤小径,雨林中的上层乔木高入云天,多为典型的热带常绿树和落叶阔叶树,树皮色浅,薄而光滑,许多发达的气根从树干悬垂下来,扎进土中又长成树干,大有一木成林的气势。波罗蜜、可可的老干长出花枝;手臂粗的野藤缠缠绕绕,沿着枝干、树丫,从一棵树爬到另外一棵树,从树下爬到树顶,又从树顶倒挂下来,交错出一道道稠密的网。附生的藻类、苔藓、地衣、蕨类以及兰科植物,仿佛披上一件厚厚的绿衣,有的还开着各种艳丽的花朵。
这里森林茂而原始,生物多而珍稀,不仅随处可见诸如植物“绞杀”、藤萝缠绕和树上生树、叶上长草、老茎生花结果等奇特景观,还有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犀牛、爪哇野牛、云豹、苏门羚、穿山甲、白鹂、犀鸟等20多种,以及中华桫椤、苏铁蕨、大叶木兰、黑黄檀等珍稀植物。这些物种起源古老,独特鲜明,是不可多得的生物资源宝库。桫椤即是其中之一。
桫椤是两亿年前地球上的居民,现在唯一残存的木本蕨类植物,堪称国宝。在远古地质时期,蕨类植物可是高大的树木,而今多为矮小草本了。
文献揭示,桫椤出现的时间比恐龙还要早一亿五千万年,在侏罗纪、白垩纪盛极一时,曾是大地上最繁盛的“蕨类植物之王”,与恐龙同生共荣(它是食草恐龙的食物)。恐龙灭绝之后,上亿种生物也一同消失,只有桫椤奇迹般地躲过寒冷的冰川期和剧烈的地壳变动,顽强地生存下来,成为缄默的“古生物活化石”。
它们的目光穿透地球历史的尘埃,目睹了恐龙的幻灭、人类的诞生和繁荣昌盛。“一树桫椤旧相识,曾经见我黑头年。”在它们的注视中,有清的诗人步履匆匆地老去;流连在树荫下的盛唐高僧,“拟扫绿阴浮佛寺,桫椤高树结为邻”;或者更早一些,释迦牟尼佛走来,在两株高大的桫椤中间铺上树叶和草,结跏趺坐,安然涅槃。这些流逝的岁月浩如烟海,但在它们的生命长河中又是何其短暂,简直不值一提。
在远离尘世喧嚣之外,它们默默地和岁月深处的自己对话:这些高古的桫椤,经过漫长的地质变迁和自然环境的改变,把自己活成“最后的侏罗纪生命”。它们是寂寞的吗?它们活得太久了,孤独地站在深山峡谷之中,我甚至听到它们发自古老生命的一声叹息。
坡陡林密,桫椤婀娜,徜徉于绿色清幽的世界里,听得见人语,却难见人影,倒是有各种动物的身影,不时从眼前掠过。性情温顺、活泼可爱的浣熊,与人非常亲近;行动特别缓慢的蜂猴,完全在树上生活,极少下地,喜欢独自活动,它是吃昆虫的猴子,可以用小棍绑上虫子喂它;长着茸角的马鹿、水鹿、梅花鹿,在丛林中繁衍栖息,它们俨然把人类当做亲密的家人。
在茂密的森林里,住着一种貌似“李逵”的动物,全身漆黑,两腮却长了雪白的胡子,它就是被称为“体操冠军”的长臂猿。它一边高声歌唱,一边在林木中不停地穿梭,将它最喜爱的香蕉远远地扔过去,又总是能准确无误地接住。
据《思茅县志》记载,这里还是白犀牛归隐之处。白犀牛浑圆粗壮,皮肤光滑,眼睛小,灵敏的耳朵可旋转,大小不一的两只角,一前一后长在鼻子上。1933年两头犀牛被捕杀事件发生后,它们好像一夜间全部离开了,此后这里再无犀牛踪迹。幸好有了近年来的科学繁育与保护,人们重又看到犀牛种群。
沿着小径往前走,一株株桫椤憋着劲儿生长,它们阅尽旷世沧桑,依然乐不知疲,显示着勃勃生机。出口几株桫椤,棕红色树干,足有碗口粗,大叶舞袖般地伸展开来,俊俏挺拔,像在迎送嘉宾,也仿佛在凝望前方野鹤翔飞的湿地。它们的眼帘里恍若充满忧伤,不知是否会闪回和恐龙在一起的甜蜜时光。风吹过,枝叶婆娑,似在轻轻诉说什么。但翘首远眺,分明连每一片叶子都是那样葱茏,翠生生、水灵灵的,绿得鲜嫩,绿得喜人,它们又是快乐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