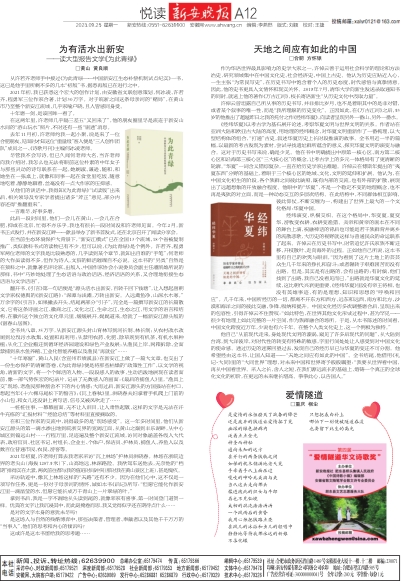发布日期:
天地之间应有如此的中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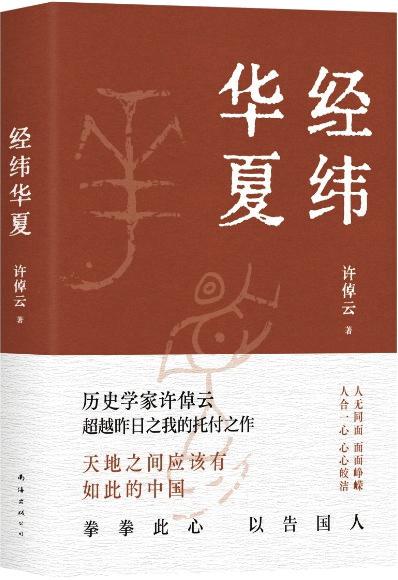
作为华语世界最具影响力的史学大家之一,许倬云善于运用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治史,研究领域集中在中国文化史、社会经济史、中国上古史。他认为历史应贴近人心,一生主张“为常民写史”,在历史书写中饱含着个人的历史态度、时代感悟与真挚情意。因此,他的史书更具人文情怀和现实关怀。2019年7月,清华大学向新生发送录取通知书的同时,就送上他的著作《万古江河》,校长寄语新生“从历史文化中汲取力量”。
许倬云曾坦露自己所从事的历史书写,并非排比岁月,也不是着眼其中的是非对错,或者某个叙事的唯一性,而是“我所理解的历史变化”。正因如此,在《万古江河》之后,93岁的他推出了超越昨日之我的托付之作《经纬华夏》,向读者呈现另外一番山、另外一番水。
《经纬华夏》以考古学为基石展开论述,考察华夏文明与世界文明的关系。作者站在亚洲大陆和欧亚古大陆的高度,用地理的经纬概念,对华夏文明重新作了一番梳理,以大型结构体的组合,“打通”古史,叙述华夏历史上长时段推演的故事。全书用近一半的篇幅,以最新的考古发现为素材,尝试寻找遗址群所蕴含的意义,探究华夏文明的演变与融合。这对于历史书写来说,确是少见。他在书中明确提出中原第一核心区、南方第二核心区和沿海第三核心区“三大核心区”的概念,让考古学上的多元一体格局有了更清晰的轮廓。“华夏”一词含义错综复杂,一直在给历史学家出难题。许倬云在傅斯年提出的“夷夏东西”分野的基础上,着眼于三个核心区的地域、文化、文明的延伸和扩展。他认为,在中国文化初生的阶段,各个族群之间彼此映照,既有内部的交流,也有外部的扩散,展现出了远超想象的开放融合程度。他眼中的“华夏”,不是一个稳定不变的地理概念,也不再是夷狄的对立面,而是一种动态交互的多层次结构。在此结构中,不同群体相互影响,彼此仰仗,不断交缠为一,构建出了世界上最大的一个文化格局:华夏中国。
经纬演变,纵横交织。在这个格局中,华变夏,夏变华,游牧变农耕,农耕变渔猎。炎帝和黄帝的剧本在不同的舞台上演,祝融神话的背后也可能是若干族群背井离乡的流散悲歌,大历史的视野就这样与普通民众的命运联系了起来。许倬云在历史书写中,时常追忆许氏家族不断迁移、开枝散叶、走向海外的过程。正如他自己所说,这本书里有自己的欢笑与眼泪,“因为看到了这片土地上的芸芸众生几千年来的挣扎和奋斗;或者辗转于艰难困苦而没有出路。但是,其实是有出路的,会有出路的;有时候,他们找到了出路,我自己没看见而已。”出路就是华夏文化的延续,这比朝代兴衰更重要。《经纬华夏》里没有帝王将相,也没有英雄事迹,有的是理想、知识和思想的“呼唤和回应”。几千年来,中国所经历的一切,都离不开东方和西方、远东和远西、南方和北方、沙漠和海洋之间的彼此交融、争锋、吸纳和提升。中国文化经历多次调整磨合后,呈现出来的包容性,引得许倬云不住赞叹:“如此特色,在世界其他文化形成过程中,甚为罕见——很少有地理上如此完整的一片空间,作为族群融合的场所。于是,从本书陈述的时间看,中国文化跨度近万年,少说也有六千年。在整个人类文化史上,这一个例极为独特。”
他自己“从前现代走来,身处现代文明的漩涡,窥见了许多后现代的问题”,从大陆到台湾,到大洋彼岸,对时代性的转变有特殊的敏感,字里行间处处让人感受到对中国文化的使命感。透过历史的迷雾回望过去,发现自己的经历早已与华夏的变迁不可分割。他希望经由这本书,让国人知道——“天地之间应有如此的中国”。全书结尾,他借用《礼记·大同》里的“大同世界”理想,对未来中国和世界寄予殷殷瞩望:“我要从世界看中国,再从中国看世界。采人之长,舍人之短,在我们源远流长的基础上,熔铸一个真正的全球化文化的初阶,在更远的未来继长增高。拳拳此心,以告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