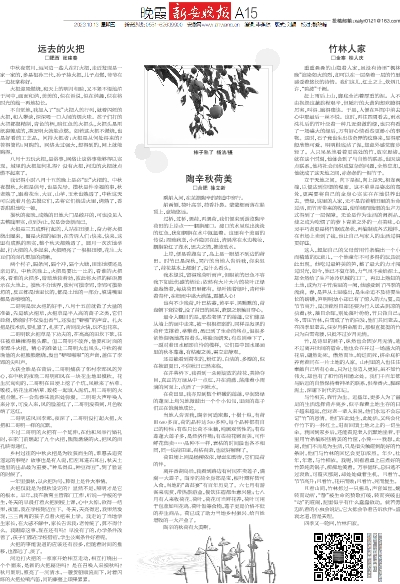发布日期:
远去的火把
中秋夜赏月,运河边一些人在打火把,走近发现是一家一家的,多是祖孙三代,孙子持火把,儿子点燃,爷爷在一边抚掌称好。
火把迎风燃烧,和天上的明月相映,又不紧不慢地泊于河中,画面和谐,美美的,似在诉说,似在谐趣,似在将时光的线一再地拉长。
不自觉地,我加入了“玩”火把人的行列,就着闪烁的火把,和人攀谈,深深吸一口人间的烟火味。孩子们打的火把都很精制,青色的柄,暗红色的火把头,火把头是用纸裹缠成的,凑近明火就能点燃。如若这火把不燃烧,也是好看的工艺品。问持火把者:火把是从何处得来的?答得简约:网购的。网络太过强大,想得到的,网上就能购得。
八月十五玩火把,是俗事,网络让这俗事能够得以实现。城里的火把如何扎得?没有火把,河边的火把就点燃不起来了。
我记得小时八月十五的晚上是必“玩”火把的。中秋夜摸秋,火把是信号,也是先导。摸秋是件幸福的事,秋老熟了,跟着花生、大豆、山芋、玉米也熟透了,中秋这天可以就着月色去摸它们,去将它们揣进火里,烤熟了,香香甜甜地吃一顿。
摸秋的夜晚,成熟的田地大门是敞开的,可也没见人去糟践果实,点到为止,仅是尝尝新而已。
火把是三五成群打起的,人站在田埂上,奋力将火把绕出圈来。圈是火把的秘语,在告诉人们:快来,快来,这里有成熟的果实,整个秋天都熟透了。圆月一次次地举起,打火把的人多起来,火把照亮了一根根田埂,花生、大豆们的面孔更加的清晰。
两个村子,隔条河,隔个冲,隔个大塘,田连地埂还是亲近的。中秋的晚上,火把是要比一比的,看谁的火把亮,看谁的火把多,暗暗地较着劲,彼此将火把的秘语展示在大地上。摸秋不分地界,张村可摸李郢,李郢可摸染坊的,反正都是地里长的,都是土地的一部分,填进嘴里都是香喷喷的。
二哥明是玩火把的好手,八月十五前就做了大量的准备,先是砍火把草,火把草是半人高的蒿子之类,它们经烧,燃烧时不仅发出香气,还发出“噼啪”的声音。扎火把是技术活,要扎紧了,扎实了,否则走火快,玩不出花来。
二哥明砍火把草是下功夫的,在高高的田坎下砍,往往被草蜂撵得抱头蹿。但二哥明不放弃,他要和对面的李郢斗火把。精心的准备让二哥明大出风头,中秋的夜晚他的火把熊熊燃烧,发出“噼哩啪啦”的声音,盖住了李郢的尖叫声。
大获全胜是在背后,二哥明捕获了邻村李郢凤的芳心,在中秋的夜晚二哥明和凤在一块花生地里摸秋。花生沉甸甸的,二哥明在田埂上挖了个坑,凤揪来了枯草、败枝,将花生和枯草、败枝一起填入泥坑,用二哥明的火把点燃,不一会焦香味就四处弥漫。二明哥大声呼唤人来分享,可没人来,凤的脸羞红了,二哥明没看到,月色收纳了这红。
二哥明送凤回李郢,夜深了,二哥明没打起火把,火把和二哥明一样的沉默。
不过二哥明的火把有一个延伸,在他和凤举行婚礼时,在家门前燃起了九个火把,熊熊燃烧的火,把凤的面孔映得通红。
乡村过往的中秋火把是为收获而生的,谁愿去追究遥远的事呢?故事也是有人说,但左耳进右耳出,秋天土地里的出品最为重要,“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到了验证的时候了。
一年里摸秋,以火把为号,算得上是件大事情。
火把仅就是为摸秋设定的?显然不是,照明才是它的根本。早年,我在教育主管部门工作,听说一学校的学生,冬天的早晨打着火把到校上课,心中大惊,欲得一结果,夜里,我在学校附近住下。冬天,天亮得迟,我果然发现,三三两两的孩子点着火把来上学。我走访了当地学生家长,在大惑不解中,家长告诉我:老传统了,算不得什么。我跟踪这事,现在还有吗?早没有了的,办学条件改善了,孩子们都在学校借宿,学生公寓条件好着呢。
火把的事能说道的应该还有很多,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也都远了、淡了。
河边打火把的一家家开始相互走动,相互打绕出一个个圈来,是新的火把秘语吗?是在召唤人来摸秋吗?秋月朗明,照亮了一河清水,一艘货船顺流而下,对着闪烁的火把拉响汽笛,河的藤蔓上硕果累累。
火把迎风燃烧,和天上的明月相映,又不紧不慢地泊于河中,画面和谐,美美的,似在诉说,似在谐趣,似在将时光的线一再地拉长。
不自觉地,我加入了“玩”火把人的行列,就着闪烁的火把,和人攀谈,深深吸一口人间的烟火味。孩子们打的火把都很精制,青色的柄,暗红色的火把头,火把头是用纸裹缠成的,凑近明火就能点燃。如若这火把不燃烧,也是好看的工艺品。问持火把者:火把是从何处得来的?答得简约:网购的。网络太过强大,想得到的,网上就能购得。
八月十五玩火把,是俗事,网络让这俗事能够得以实现。城里的火把如何扎得?没有火把,河边的火把就点燃不起来了。
我记得小时八月十五的晚上是必“玩”火把的。中秋夜摸秋,火把是信号,也是先导。摸秋是件幸福的事,秋老熟了,跟着花生、大豆、山芋、玉米也熟透了,中秋这天可以就着月色去摸它们,去将它们揣进火里,烤熟了,香香甜甜地吃一顿。
摸秋的夜晚,成熟的田地大门是敞开的,可也没见人去糟践果实,点到为止,仅是尝尝新而已。
火把是三五成群打起的,人站在田埂上,奋力将火把绕出圈来。圈是火把的秘语,在告诉人们:快来,快来,这里有成熟的果实,整个秋天都熟透了。圆月一次次地举起,打火把的人多起来,火把照亮了一根根田埂,花生、大豆们的面孔更加的清晰。
两个村子,隔条河,隔个冲,隔个大塘,田连地埂还是亲近的。中秋的晚上,火把是要比一比的,看谁的火把亮,看谁的火把多,暗暗地较着劲,彼此将火把的秘语展示在大地上。摸秋不分地界,张村可摸李郢,李郢可摸染坊的,反正都是地里长的,都是土地的一部分,填进嘴里都是香喷喷的。
二哥明是玩火把的好手,八月十五前就做了大量的准备,先是砍火把草,火把草是半人高的蒿子之类,它们经烧,燃烧时不仅发出香气,还发出“噼啪”的声音。扎火把是技术活,要扎紧了,扎实了,否则走火快,玩不出花来。
二哥明砍火把草是下功夫的,在高高的田坎下砍,往往被草蜂撵得抱头蹿。但二哥明不放弃,他要和对面的李郢斗火把。精心的准备让二哥明大出风头,中秋的夜晚他的火把熊熊燃烧,发出“噼哩啪啦”的声音,盖住了李郢的尖叫声。
大获全胜是在背后,二哥明捕获了邻村李郢凤的芳心,在中秋的夜晚二哥明和凤在一块花生地里摸秋。花生沉甸甸的,二哥明在田埂上挖了个坑,凤揪来了枯草、败枝,将花生和枯草、败枝一起填入泥坑,用二哥明的火把点燃,不一会焦香味就四处弥漫。二明哥大声呼唤人来分享,可没人来,凤的脸羞红了,二哥明没看到,月色收纳了这红。
二哥明送凤回李郢,夜深了,二哥明没打起火把,火把和二哥明一样的沉默。
不过二哥明的火把有一个延伸,在他和凤举行婚礼时,在家门前燃起了九个火把,熊熊燃烧的火,把凤的面孔映得通红。
乡村过往的中秋火把是为收获而生的,谁愿去追究遥远的事呢?故事也是有人说,但左耳进右耳出,秋天土地里的出品最为重要,“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到了验证的时候了。
一年里摸秋,以火把为号,算得上是件大事情。
火把仅就是为摸秋设定的?显然不是,照明才是它的根本。早年,我在教育主管部门工作,听说一学校的学生,冬天的早晨打着火把到校上课,心中大惊,欲得一结果,夜里,我在学校附近住下。冬天,天亮得迟,我果然发现,三三两两的孩子点着火把来上学。我走访了当地学生家长,在大惑不解中,家长告诉我:老传统了,算不得什么。我跟踪这事,现在还有吗?早没有了的,办学条件改善了,孩子们都在学校借宿,学生公寓条件好着呢。
火把的事能说道的应该还有很多,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也都远了、淡了。
河边打火把的一家家开始相互走动,相互打绕出一个个圈来,是新的火把秘语吗?是在召唤人来摸秋吗?秋月朗明,照亮了一河清水,一艘货船顺流而下,对着闪烁的火把拉响汽笛,河的藤蔓上硕果累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