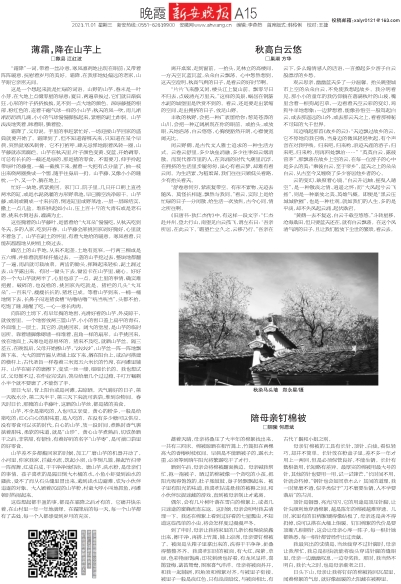发布日期:
薄霜,降在山芋上
“霜降”一词,带着一丝冷意,寒风凛冽地出现在眼前;又带着阵阵暖意,抚慰着岁月的美好。霜降,在我那地处偏远的老家,山芋跟它亲密无间。
这是一个想起来就是忙碌的词语。山野的山芋,春末是一叶小芽,在大地上点缀零星的绿意;夏日,两遍草拔过,它们就日渐疯狂,心形的叶子挤挤挨挨,见不到一点大地的颜色。深绿藤蔓的根部,粉红色的,连着干瘪气球一样的小山芋;秋天的风一吹,雨儿淅淅沥沥洒几滴,小小的气球慢慢膨胀起来,紧绷的泥土炸裂。山芋浅浅地笑着,眯着眼,腆着脸。
霜降了,父母说。手里的事赶紧忙好,一场迎接山芋回家的盛典就要开始了。霜降到了,但不知道霜哪天来,只知道在某个早晨,突然就寒风刺骨。它不打招呼,肆无忌惮地跟着风转一圈,山芋藤就冻黑腐烂。山芋在秋天里,叶子颜色变黄、变蓝,开始凋零,可总有长长的一截还是绿的,那是猪的零食。不需要刀,伸手拎起带绿叶的藤蔓,一截一截拽下来,握着一大把有点分量了,抽一枝出来绕两圈挽成一个髻,随手往身后一扔。山芋藤,又像小小的睡枕,一个,又一个,躺在地上。
忙好一块地,抓紧挑回。家门口,院子里,几只开口朝上直径两米的缸,或是水泥浇灌的方形野菜池,早已腾空洗净晾干。山芋藤,或剁或铡成一寸来长的,倒进缸里或野菜池,一层一层踩结实,撒上一点儿盐。堆积拱起如小山,压上百十斤的大青石或是老石磨,挑来水倒进去,灌满为止。
这些腌着的山芋藤叶,是留着给“大耳朵”慢慢吃,从秋天吃到冬天,多的人家,吃到开春。山芋藤全部挑回家剁好腌好,心里就不着急了。山芋在泥土的怀里,有着大地给的暖意。寒风看着,只能灰溜溜地从树梢上绕过去。
峰峦上的山芋地,从来不起垄,土地有宽窄,一行两三棵或是五六棵,并排着就那样扦插过去。一垄的山芋挖过去,整块地都翻了一遍,雨后就可栽油菜。两齿的锄头,挥舞起来轻松,泥土漏过去,山芋露出来。有时一锄头下去,锄齿卡在山芋里,痛心。好好的一个大山芋就两半了,心里也凉了一点。泥土里的事情,确实难把握。破碎的,也没啥的,挑回家先吃就是。猪栏的几头“大耳朵”,一百来斤,瘦瘦长长的,猪坯已成。等着山芋到来,一桶一桶地倒下去,长鼻子闷进猪食槽“咕噜咕噜”“咣当咣当”,头都不抬。吃饱了睡,睡醒了吃,一心一意长肉肉。
向阳的土塝下,有早年掏的地窖,光滑好看的山芋,外皮晾干,就放窖里。一个地窖放两三篮山芋,小小的窖口盖上扁平的青石,外面堆上一层土。其它的,就挑回家。阔大的堂屋,是山芋的临时居所。靠着墙脚像砌墙一样堆着,直角一样的扇形。山芋挑回来,放在地面上,天寒也是容易坏的。猪来不及吃,就晒山芋丝。隔三差五,在晚饭后,父母开始擦山芋,“沙沙沙”,山芋丝一阵一阵地飘落下来。大大的圆竹匾从老墙上取下来,搁在阳台上,或沿河搭建的横杆上;古代圣旨一样卷着三米宽五六米长的竹席,在河滩里铺开。山芋在刷子的磨擦下,变成一丝一缕,细细长长的。我也想试试,父母拗不过,在作业完成后,答应给磨几个过过瘾,千叮万嘱剩小半个就不要磨了,不能伤了手。
翌日大早,背上阳台或是河滩,去晾晒。天气晴好的日子,第一天收水分,第二天半干,第三天下来就可装袋,堆到杂物间。春天时日长,那腌的山芋藤叶,这晒的山芋丝,都是猪的美食。
山芋,不全是猪吃的,人也可以享受。黄心的粉多,一般是给猪吃的;红心白心的甜味重,是人吃的。在没有多少糖可以供应、没有零食可以买的时代,白心的山芋,放一段时间,煮熟时香气裹挟着甜味,柔软的味道,就是“山珍”。黄心山芋煮熟后,切成条晒干之后,非常甜,有韧性,有着好听的名字“山芋枣”,是可揣口袋里的好零食。
山芋差不多都搬回家的时候,加工厂磨山芋的机器开动了。小河里,你家我家,拦截水流,筑起小坝,山芋倒几篮,操起竹扫帚一阵挥舞,红皮白皮,干干净净地仰泳。磨山芋,洗水粉,是母亲们的事情。孩子喜欢的是隔日倒大木桶的水,小鱼小虾受到浊水的骚扰,受不了而从石头缝里冒出来,逃到浅水边避难,成为小伙伴追逐的对象。大人顾着沉淀的山芋粉,村童大呼小叫地抓鱼,河滩顿时热闹起来。
这些想起都丰盈的事,都是在霜降之后才有的。它痛并快乐着,在山村里一年一年地演绎。在霜降后的每一天,每一个山芋都有了去处,每一个人都感受到岁月的充实。
这是一个想起来就是忙碌的词语。山野的山芋,春末是一叶小芽,在大地上点缀零星的绿意;夏日,两遍草拔过,它们就日渐疯狂,心形的叶子挤挤挨挨,见不到一点大地的颜色。深绿藤蔓的根部,粉红色的,连着干瘪气球一样的小山芋;秋天的风一吹,雨儿淅淅沥沥洒几滴,小小的气球慢慢膨胀起来,紧绷的泥土炸裂。山芋浅浅地笑着,眯着眼,腆着脸。
霜降了,父母说。手里的事赶紧忙好,一场迎接山芋回家的盛典就要开始了。霜降到了,但不知道霜哪天来,只知道在某个早晨,突然就寒风刺骨。它不打招呼,肆无忌惮地跟着风转一圈,山芋藤就冻黑腐烂。山芋在秋天里,叶子颜色变黄、变蓝,开始凋零,可总有长长的一截还是绿的,那是猪的零食。不需要刀,伸手拎起带绿叶的藤蔓,一截一截拽下来,握着一大把有点分量了,抽一枝出来绕两圈挽成一个髻,随手往身后一扔。山芋藤,又像小小的睡枕,一个,又一个,躺在地上。
忙好一块地,抓紧挑回。家门口,院子里,几只开口朝上直径两米的缸,或是水泥浇灌的方形野菜池,早已腾空洗净晾干。山芋藤,或剁或铡成一寸来长的,倒进缸里或野菜池,一层一层踩结实,撒上一点儿盐。堆积拱起如小山,压上百十斤的大青石或是老石磨,挑来水倒进去,灌满为止。
这些腌着的山芋藤叶,是留着给“大耳朵”慢慢吃,从秋天吃到冬天,多的人家,吃到开春。山芋藤全部挑回家剁好腌好,心里就不着急了。山芋在泥土的怀里,有着大地给的暖意。寒风看着,只能灰溜溜地从树梢上绕过去。
峰峦上的山芋地,从来不起垄,土地有宽窄,一行两三棵或是五六棵,并排着就那样扦插过去。一垄的山芋挖过去,整块地都翻了一遍,雨后就可栽油菜。两齿的锄头,挥舞起来轻松,泥土漏过去,山芋露出来。有时一锄头下去,锄齿卡在山芋里,痛心。好好的一个大山芋就两半了,心里也凉了一点。泥土里的事情,确实难把握。破碎的,也没啥的,挑回家先吃就是。猪栏的几头“大耳朵”,一百来斤,瘦瘦长长的,猪坯已成。等着山芋到来,一桶一桶地倒下去,长鼻子闷进猪食槽“咕噜咕噜”“咣当咣当”,头都不抬。吃饱了睡,睡醒了吃,一心一意长肉肉。
向阳的土塝下,有早年掏的地窖,光滑好看的山芋,外皮晾干,就放窖里。一个地窖放两三篮山芋,小小的窖口盖上扁平的青石,外面堆上一层土。其它的,就挑回家。阔大的堂屋,是山芋的临时居所。靠着墙脚像砌墙一样堆着,直角一样的扇形。山芋挑回来,放在地面上,天寒也是容易坏的。猪来不及吃,就晒山芋丝。隔三差五,在晚饭后,父母开始擦山芋,“沙沙沙”,山芋丝一阵一阵地飘落下来。大大的圆竹匾从老墙上取下来,搁在阳台上,或沿河搭建的横杆上;古代圣旨一样卷着三米宽五六米长的竹席,在河滩里铺开。山芋在刷子的磨擦下,变成一丝一缕,细细长长的。我也想试试,父母拗不过,在作业完成后,答应给磨几个过过瘾,千叮万嘱剩小半个就不要磨了,不能伤了手。
翌日大早,背上阳台或是河滩,去晾晒。天气晴好的日子,第一天收水分,第二天半干,第三天下来就可装袋,堆到杂物间。春天时日长,那腌的山芋藤叶,这晒的山芋丝,都是猪的美食。
山芋,不全是猪吃的,人也可以享受。黄心的粉多,一般是给猪吃的;红心白心的甜味重,是人吃的。在没有多少糖可以供应、没有零食可以买的时代,白心的山芋,放一段时间,煮熟时香气裹挟着甜味,柔软的味道,就是“山珍”。黄心山芋煮熟后,切成条晒干之后,非常甜,有韧性,有着好听的名字“山芋枣”,是可揣口袋里的好零食。
山芋差不多都搬回家的时候,加工厂磨山芋的机器开动了。小河里,你家我家,拦截水流,筑起小坝,山芋倒几篮,操起竹扫帚一阵挥舞,红皮白皮,干干净净地仰泳。磨山芋,洗水粉,是母亲们的事情。孩子喜欢的是隔日倒大木桶的水,小鱼小虾受到浊水的骚扰,受不了而从石头缝里冒出来,逃到浅水边避难,成为小伙伴追逐的对象。大人顾着沉淀的山芋粉,村童大呼小叫地抓鱼,河滩顿时热闹起来。
这些想起都丰盈的事,都是在霜降之后才有的。它痛并快乐着,在山村里一年一年地演绎。在霜降后的每一天,每一个山芋都有了去处,每一个人都感受到岁月的充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