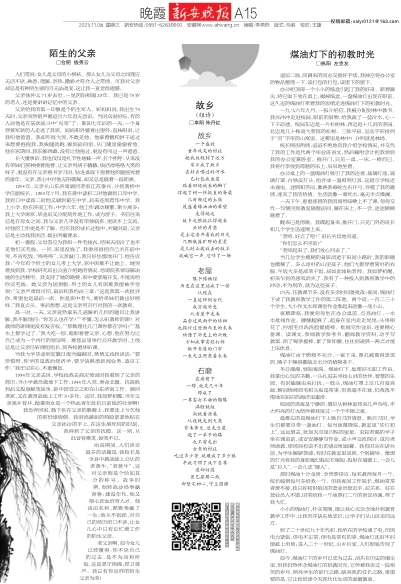发布日期:
陌生的父亲
人们常说:女儿是父母的小棉袄。那么女儿与父母之间理应无话不谈,熟悉、理解、亲热、撒娇才符合人之常情。可我对父亲却总是有种陌生感而且无法改变,这让我一直觉得遗憾。
父亲钱仲义71岁去世,一晃阴阳相隔29年。我已是78岁的老人,还是要讲讲记忆中的父亲。
父亲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个陌生军人。听妈妈说,我出生70天时,父亲突然销声匿迹且六年杳无音讯。当时众说纷纭,有的人说他是在某次战斗中“光荣”了。谁知七年后的一天,一个身穿黄军装的人走进了我家。妈妈和外婆喜出望外、直抹眼泪,让我叫他爸爸。我却吓得大哭,不敢见他。他拿着糖和饼干送过来想要抱抱我,我拔腿就跑,躲到房间里,从门缝里偷偷看他。他在家期间,我东躲西藏,没有让他抱过,更没有叫过一声爸爸。
长大懂事后,我也仅仅是礼节性地喊一声,打个招呼,从来没有弟妹们那种搂着抱着、让父亲用胡子戳戳,快活得咯咯大笑的样子,更没有在父亲看书学习时,钻进桌底下抱着他的腿摇晃着的童年。父亲,我心中对他无限敬佩,却又总是隔着一段距离。
1958年,父亲从山东济南调回老家江苏泰兴,分到黄桥中学任副校长。1960年7月,我在黄中读初二时他调到口岸中学,我到口中读高二时他又调到霍庄中学,后来还到蒋华中学。我上小学,他在济南工作;中学六年,他工作调动频繁,聚少离多;我上大学离家,毕业后又分配到外地工作,成为游子。书信往来总是在母女之间,我与父亲几乎没有单独联系,更谈不上交流,对他的工作更是不了解。但在我的成长过程中,关键时刻,父亲总是主动找我谈话,提出明确要求。
初一暑假,父母答应为我织一件毛线衣,结果天很冷了也不见他们买毛线。一问,家里没钱了,我委屈得把自己关在房中哭,不肯吃饭。“咚咚咚”,父亲敲门,我只好怯懦地开门,他告诉我:“今年有个烈士的女儿考上大学,家中困难不让她上。她哭着找到我,学校研究后出公函介绍她的情况,恳请院系领导解决她的生活费用。我支持了她的路费,家中要紧缩开支,不能再给你买毛线。她父亲为国捐躯,烈士的女儿有困难我能袖手旁观?”父亲严肃得可怕,最后和我约法三章:“这是我第一次批评你,希望也是最后一次。你是家中老大,要给弟妹们做出好榜样。”我直点头。事后想想,这是父亲用言行对我的一次教育。
高一时,一天,父亲竟然拿来几道解析几何的题目让我讲解,我不解地问:“你怎么也在学?”“不懂,怎么听教师的课?对教师的讲课更没有发言权。”“那数理化几门课你都在学吗?”“基本上都学过了。”我大吃一惊,瞪眼看着父亲,心想,他在努力让自己成为一个内行的领导呀。难怪县里举行公开教学时,上级总是让父亲任听课组组长,到各校循环听课。
当我大学毕业到安徽日报当编辑时,爸爸又找我谈话:“要珍惜呀,你学的是政治经济学,要尽快熟悉新闻业务,适应工作。”我牢记在心,不敢懈怠。
1994年父亲去世,学校找我去商定悼词时我看到了父亲的简历:当小学教员做地下工作,1944年入党,奉命北撤。抗战胜利后又投身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之初在山东济南工作。调回老家,又在教育战线上工作30多年。这时,我如梦初醒,当年父亲离乡背井、抛妻别女是一个热血青年赴抗日前线的壮举啊!我急奔回家,跪下伏在父亲的胳膊上,我要还上亏欠他的那份感情债。我泪流满面的热脸紧紧地贴在父亲冰冷的手上,在这生离死别的时刻,我得到了父亲的抚摸。这一别,从此音容难觅,恸哭不已。
治丧期间,人们谈论最多的话题是,钱校长是全县中教战线上公认的老黄牛。“老黄牛”,这对父亲倒是个恰如其分的称号。战争时期,他转战沙场奉献青春;建设年代,他又呕心沥血培育人才。他淡泊名利,默默奉献了一生;他从不张扬,对自己的经历闭口不谈,让女儿心中只有位忙着工作的陌生父亲。
老父亲啊,如今女儿已经懂得:你不谈自己的过去,是不为功利所役,这是坚守情操,捍卫尊严。我以有你这样的陌生父亲为荣!
父亲钱仲义71岁去世,一晃阴阳相隔29年。我已是78岁的老人,还是要讲讲记忆中的父亲。
父亲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个陌生军人。听妈妈说,我出生70天时,父亲突然销声匿迹且六年杳无音讯。当时众说纷纭,有的人说他是在某次战斗中“光荣”了。谁知七年后的一天,一个身穿黄军装的人走进了我家。妈妈和外婆喜出望外、直抹眼泪,让我叫他爸爸。我却吓得大哭,不敢见他。他拿着糖和饼干送过来想要抱抱我,我拔腿就跑,躲到房间里,从门缝里偷偷看他。他在家期间,我东躲西藏,没有让他抱过,更没有叫过一声爸爸。
长大懂事后,我也仅仅是礼节性地喊一声,打个招呼,从来没有弟妹们那种搂着抱着、让父亲用胡子戳戳,快活得咯咯大笑的样子,更没有在父亲看书学习时,钻进桌底下抱着他的腿摇晃着的童年。父亲,我心中对他无限敬佩,却又总是隔着一段距离。
1958年,父亲从山东济南调回老家江苏泰兴,分到黄桥中学任副校长。1960年7月,我在黄中读初二时他调到口岸中学,我到口中读高二时他又调到霍庄中学,后来还到蒋华中学。我上小学,他在济南工作;中学六年,他工作调动频繁,聚少离多;我上大学离家,毕业后又分配到外地工作,成为游子。书信往来总是在母女之间,我与父亲几乎没有单独联系,更谈不上交流,对他的工作更是不了解。但在我的成长过程中,关键时刻,父亲总是主动找我谈话,提出明确要求。
初一暑假,父母答应为我织一件毛线衣,结果天很冷了也不见他们买毛线。一问,家里没钱了,我委屈得把自己关在房中哭,不肯吃饭。“咚咚咚”,父亲敲门,我只好怯懦地开门,他告诉我:“今年有个烈士的女儿考上大学,家中困难不让她上。她哭着找到我,学校研究后出公函介绍她的情况,恳请院系领导解决她的生活费用。我支持了她的路费,家中要紧缩开支,不能再给你买毛线。她父亲为国捐躯,烈士的女儿有困难我能袖手旁观?”父亲严肃得可怕,最后和我约法三章:“这是我第一次批评你,希望也是最后一次。你是家中老大,要给弟妹们做出好榜样。”我直点头。事后想想,这是父亲用言行对我的一次教育。
高一时,一天,父亲竟然拿来几道解析几何的题目让我讲解,我不解地问:“你怎么也在学?”“不懂,怎么听教师的课?对教师的讲课更没有发言权。”“那数理化几门课你都在学吗?”“基本上都学过了。”我大吃一惊,瞪眼看着父亲,心想,他在努力让自己成为一个内行的领导呀。难怪县里举行公开教学时,上级总是让父亲任听课组组长,到各校循环听课。
当我大学毕业到安徽日报当编辑时,爸爸又找我谈话:“要珍惜呀,你学的是政治经济学,要尽快熟悉新闻业务,适应工作。”我牢记在心,不敢懈怠。
1994年父亲去世,学校找我去商定悼词时我看到了父亲的简历:当小学教员做地下工作,1944年入党,奉命北撤。抗战胜利后又投身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之初在山东济南工作。调回老家,又在教育战线上工作30多年。这时,我如梦初醒,当年父亲离乡背井、抛妻别女是一个热血青年赴抗日前线的壮举啊!我急奔回家,跪下伏在父亲的胳膊上,我要还上亏欠他的那份感情债。我泪流满面的热脸紧紧地贴在父亲冰冷的手上,在这生离死别的时刻,我得到了父亲的抚摸。这一别,从此音容难觅,恸哭不已。
治丧期间,人们谈论最多的话题是,钱校长是全县中教战线上公认的老黄牛。“老黄牛”,这对父亲倒是个恰如其分的称号。战争时期,他转战沙场奉献青春;建设年代,他又呕心沥血培育人才。他淡泊名利,默默奉献了一生;他从不张扬,对自己的经历闭口不谈,让女儿心中只有位忙着工作的陌生父亲。
老父亲啊,如今女儿已经懂得:你不谈自己的过去,是不为功利所役,这是坚守情操,捍卫尊严。我以有你这样的陌生父亲为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