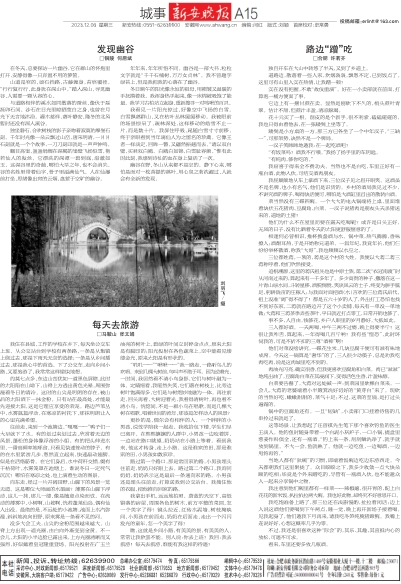发布日期:
路边“蹭”吃
独自开车在大山中转悠了半天,又到了乡道上。
道路边,散落着一些人家,炊烟袅袅,飘忽不定,已到饭点了。这里可有山里人实在热情,让我蹭一顿?
实在没有把握,不敢“故伎重演”。好在一小卖部就在前面,打算泡一桶方便面了事。
它边上有一捆甘蔗在卖。显然是刚砍下不久的,梢头蔗叶青翠。估计不甜,但蔗汁丰盈,清凉解渴。
花十元买了一根。削皮的是个新手,很不利索,磕磕碰碰的,我也只得由着他去,在一张矮凳上坐等了。
矮凳是小方桌的一方,那三方已各坐了一个中年汉子。“三缺一”,可那架势,决然不是一个牌局。
一汉子笑眯眯地邀我:在一起吃酒吧?
“有饭菜吗?酒我不行哦。”我扬了扬手里的车钥匙。
“有炖肉,够你吃的。”
我窃喜于得来全不费功夫。当然也不是白吃,车里正好有一瓶白酒,此物入伙,可结交酒肉朋友。
我屁颠颠地从车上拿酒下来,三位汉子见之眉开眼笑。这酒虽不是名牌,也小有名气,他们是识货的。乡村的酒局我见过不少,不讲究酒的牌子,喝得快活便可,哪怕是大酒缸里舀出的散装白酒。
菜当然没有三碟四碗。一个大大的电火锅端将上桌,里面堆着块状五花猪肉、豆腐角、白菜。一汉子说猪肉是朋友头天杀猪送来的,道地的土猪!
他们为什么不在屋里而要在露天吃喝呢?或许是日头正好,无风的日子,没有比晒着冬天的太阳更舒服惬意的了。
相逢何必曾相识,推杯换盏酒与水。锅中菜,热气腾腾,香味撩人;酒酣耳热,于是开始称兄道弟。一叙年纪,我竟年长,他们仨纷纷举杯敬酒,称我“大哥”,我也频频以水应之。
三位都姓蒋,一族的,蒋是这个村的大姓。我便以大蒋二蒋三蒋称呼着,他们欣然接受。
追根溯源,这里的蒋氏祖先也是中原士族,第二次“衣冠南渡”时从河南过来的,算起来有一千多年了。多少高贵的种子,撒落在这一片青山绿水间,斗转星移,洒脱倜傥、笑谈风云的士子,终变为胼手胝足、躬耕陇亩的庄稼人;与我面对面把酒(水)言欢的三位蒋氏后代,祖上没准“阔”得不得了!都是五六十岁的人了,外出打工恐怕也找不到好东家,二蒋就在路边开了这个小卖铺,每天有一单没一单地做;大蒋和三蒋茶季弄些茶叶,平日就近打点零工,日常开销也够了。
事不多,人自由,钱够花,乡户人眼里的岁月静好,大抵如此。
三人都好酒。一天两喝,中午三两不过瘾,晚上得要半斤!这很让我咋舌,算起来,一年得喝几百斤呐!我有些“惶恐”,此时环伺我的,可是不折不扣的三尊“酒神”啊!
他们对菜没啥讲究,一碟花生米,几块豆腐干便可有滋有味地成席。今天这一锅算是“奢华”的了,三人很少动筷子,总是劝我吃肉吃肉,说是这肉城里吃不到的。
肉油光闪亮,确实很香,但我更喜欢豆腐角和白菜。肉已“滋滋”地炖出油了,豆腐角白菜在其浸润下,变得活色生香,汁盈味醇。
白菜要告罄了,大蒋对远处喊一声:到菜园里砍棵白菜来。一会儿,大蒋的老婆端着小半簸箕洗好切好的“黄芽白”来了。现砍的当然好吃,嫩嫩甜甜的,菜气十足;不过,这菜的至境,是打过头遍霜的。
锅中的豆腐角还有。一旦“短缺”,小卖部门口挂着待售的几串拎过来就是了。
这等场景,让我想起了汪曾祺先生笔下那个喜欢钓鱼的医生王淡人。他钓鱼时随身带着一个白泥小灰炉子,一口小锅,提盒里葱姜作料俱全,还有一瓶酒。“钓上来一条,刮刮鳞洗净了,就手就放到锅里。不大一会,鱼就熟了。他就一边吃鱼,一边喝酒,一边甩钩再钓。”
当地人都有“驮碗”的习惯,即端着饭碗边吃边东游西走。今天都朝我们这里聚拢了。众目睽睽之下,我多少收敛一点大快朵颐的吃相;毕竟是个外来蹭吃的,尽管有一瓶酒入伙,也不能邀众人一起来分享锅中之物。
我注意到他们碗里都有一样菜——辣椒瘪,很开胃的,配上白花花的新米饭,扒拉扒拉两大碗。我也好此物,却终究不好意思开口。
我吃饱准备上路了,那三位还在浅斟慢酌,扯拉着闲话;边上人说这酒他们要喝到下午两点,睡一觉,晚上再开新场子接着喝。见我起身了,他们邀我下月再来,请我吃冬笋炖腌猪蹄腕。我嘴上连说好好,心想这概率几乎为零。
不过,我还是很喜欢这种“际会”的,其乐、其趣、其直抵内心的放松,可遇不可求。
看来,车里还要多放几瓶酒。
道路边,散落着一些人家,炊烟袅袅,飘忽不定,已到饭点了。这里可有山里人实在热情,让我蹭一顿?
实在没有把握,不敢“故伎重演”。好在一小卖部就在前面,打算泡一桶方便面了事。
它边上有一捆甘蔗在卖。显然是刚砍下不久的,梢头蔗叶青翠。估计不甜,但蔗汁丰盈,清凉解渴。
花十元买了一根。削皮的是个新手,很不利索,磕磕碰碰的,我也只得由着他去,在一张矮凳上坐等了。
矮凳是小方桌的一方,那三方已各坐了一个中年汉子。“三缺一”,可那架势,决然不是一个牌局。
一汉子笑眯眯地邀我:在一起吃酒吧?
“有饭菜吗?酒我不行哦。”我扬了扬手里的车钥匙。
“有炖肉,够你吃的。”
我窃喜于得来全不费功夫。当然也不是白吃,车里正好有一瓶白酒,此物入伙,可结交酒肉朋友。
我屁颠颠地从车上拿酒下来,三位汉子见之眉开眼笑。这酒虽不是名牌,也小有名气,他们是识货的。乡村的酒局我见过不少,不讲究酒的牌子,喝得快活便可,哪怕是大酒缸里舀出的散装白酒。
菜当然没有三碟四碗。一个大大的电火锅端将上桌,里面堆着块状五花猪肉、豆腐角、白菜。一汉子说猪肉是朋友头天杀猪送来的,道地的土猪!
他们为什么不在屋里而要在露天吃喝呢?或许是日头正好,无风的日子,没有比晒着冬天的太阳更舒服惬意的了。
相逢何必曾相识,推杯换盏酒与水。锅中菜,热气腾腾,香味撩人;酒酣耳热,于是开始称兄道弟。一叙年纪,我竟年长,他们仨纷纷举杯敬酒,称我“大哥”,我也频频以水应之。
三位都姓蒋,一族的,蒋是这个村的大姓。我便以大蒋二蒋三蒋称呼着,他们欣然接受。
追根溯源,这里的蒋氏祖先也是中原士族,第二次“衣冠南渡”时从河南过来的,算起来有一千多年了。多少高贵的种子,撒落在这一片青山绿水间,斗转星移,洒脱倜傥、笑谈风云的士子,终变为胼手胝足、躬耕陇亩的庄稼人;与我面对面把酒(水)言欢的三位蒋氏后代,祖上没准“阔”得不得了!都是五六十岁的人了,外出打工恐怕也找不到好东家,二蒋就在路边开了这个小卖铺,每天有一单没一单地做;大蒋和三蒋茶季弄些茶叶,平日就近打点零工,日常开销也够了。
事不多,人自由,钱够花,乡户人眼里的岁月静好,大抵如此。
三人都好酒。一天两喝,中午三两不过瘾,晚上得要半斤!这很让我咋舌,算起来,一年得喝几百斤呐!我有些“惶恐”,此时环伺我的,可是不折不扣的三尊“酒神”啊!
他们对菜没啥讲究,一碟花生米,几块豆腐干便可有滋有味地成席。今天这一锅算是“奢华”的了,三人很少动筷子,总是劝我吃肉吃肉,说是这肉城里吃不到的。
肉油光闪亮,确实很香,但我更喜欢豆腐角和白菜。肉已“滋滋”地炖出油了,豆腐角白菜在其浸润下,变得活色生香,汁盈味醇。
白菜要告罄了,大蒋对远处喊一声:到菜园里砍棵白菜来。一会儿,大蒋的老婆端着小半簸箕洗好切好的“黄芽白”来了。现砍的当然好吃,嫩嫩甜甜的,菜气十足;不过,这菜的至境,是打过头遍霜的。
锅中的豆腐角还有。一旦“短缺”,小卖部门口挂着待售的几串拎过来就是了。
这等场景,让我想起了汪曾祺先生笔下那个喜欢钓鱼的医生王淡人。他钓鱼时随身带着一个白泥小灰炉子,一口小锅,提盒里葱姜作料俱全,还有一瓶酒。“钓上来一条,刮刮鳞洗净了,就手就放到锅里。不大一会,鱼就熟了。他就一边吃鱼,一边喝酒,一边甩钩再钓。”
当地人都有“驮碗”的习惯,即端着饭碗边吃边东游西走。今天都朝我们这里聚拢了。众目睽睽之下,我多少收敛一点大快朵颐的吃相;毕竟是个外来蹭吃的,尽管有一瓶酒入伙,也不能邀众人一起来分享锅中之物。
我注意到他们碗里都有一样菜——辣椒瘪,很开胃的,配上白花花的新米饭,扒拉扒拉两大碗。我也好此物,却终究不好意思开口。
我吃饱准备上路了,那三位还在浅斟慢酌,扯拉着闲话;边上人说这酒他们要喝到下午两点,睡一觉,晚上再开新场子接着喝。见我起身了,他们邀我下月再来,请我吃冬笋炖腌猪蹄腕。我嘴上连说好好,心想这概率几乎为零。
不过,我还是很喜欢这种“际会”的,其乐、其趣、其直抵内心的放松,可遇不可求。
看来,车里还要多放几瓶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