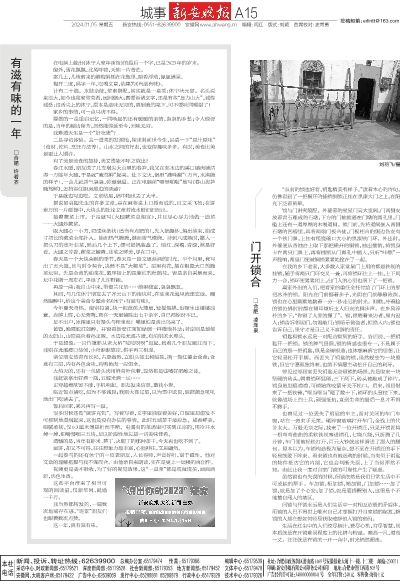发布日期:
有滋有味的一年□
在电脑上敲出《休宁人家年夜饭》的最后一个字,已是2023年的岁末。
窗外,雪花飘飘,北风呼啸,天地一片苍茫。
案几上,几枝剪来的腊梅斜插在花瓶里,暗香浮动,氤氲满屋。
梅开二度,码字一年,吃喝文章,结集为《有滋有味》。
计有二十篇。水陆杂陈,荤素搭配,其实就是一桌菜:休宁状元宴。名头说来很大,如今也是家常菜肴,民间烟火;真要诉诸文字,还是有些“压力山大”,诚惶诚恐:这舌尖上的休宁,原本是滋味无穷的,落到我的笔下,可不要味同嚼蜡了!
家乡的事情,可一点马虎不得。
要做的一是重启记忆,一同唤起的还有暖暖的亲情,袅袅的乡愁;令人惊讶的是,当年的颊齿留芳,居然能绵延至今,回味无穷。
我难道天生是一个“好吃佬”?
二是寻访体验。去一道菜的发源地,探求其前世今生,品尝一下“原汁原味”(食材、佐料、烹饪方法等)。山水之间的行走,也变得趣味多多。有时,美食比美景更让人期许。
有了美景美食的加持,美文焉能不呼之欲出?
春江水暖,朋友送了几支璜尖大山里的春笋,我又在率水边的溪口镇肉铺沽得一方陈年火腿,于是就“腌笃鲜”起来。灶下文火,锅里“滴哚翻”(方言,水沸腾的样子),一会儿就香气袅袅,弥漫满屋。正在电脑前“噼里啪啦”地写《春山拔笋腌笃鲜》,怎挡得住厨房那边的诱惑?
于是就边写边吃。文章结尾,锅中物也去了大半。
据说梁启超先生的许多文章,是在麻将桌上口授而成的,且文采飞扬;在饼索万的一片碰撞中,大块头的社论文章若流水般汩汩而出。
接着蕨菜上市。于是就写《火腿蕨菜总相宜》,并且尽心尽力地做一道菜——火腿炒蕨菜。
取火腿心一小方,切成丝条状(适当有点肥的),先入锅爆炒,煸出油来,掐成寸把长的蕨菜全部扑入。始而热气腾腾,继而香气缭绕。待到八成熟时,撒入一把头刀的宽叶韭菜,然后几个上下,便可起锅装盘了。暗红、深褐、青绿,煞是好看。火腿之芳香、蕨菜之嫩爽、韭菜之鲜美,尽在口中。
春天是一个大快朵颐的季节,春天是一段文思汹涌的时光。半个月里,竟写出了五六篇,且与时令契合,决然不是“大棚菜”。屋里有花,插在粗瓷大口的腌菜坛里。先是金黄的油菜花,循序接上的是紫红的杜鹃花。皆是亲自采集而来,坛中花期一周左右,平添了几许野趣。
再放一曲:我自山中来,带着兰花草……缭梁绕室,袅袅飘忽。
其间,与几位休宁朋友去了齐云山下的南坑村,在油菜花海里流连忘返。醺然陶醉中,给这个美食专题命名《休宁·有滋有味》。
今年夏天奇热。窗帘拉紧,执一把芭蕉大蒲扇,轻摇慢拂,也顿生出缕缕凉意。赤膊上阵,心无旁骛,竟在一天里铺陈出七千余字,自己都惊讶不已。
足不出户,冰箱里只有馒头与榨菜矣!嘴里怕是淡出鸟来了。
黄昏,晚霞酡红如醉。开窗看新安江面如绿绸一样微微抖动;对岸则是葱郁的太阳山,山顶高耸着孙王阁。水边是尤溪古渡,有泊船的水埠头。
于是想象:一只竹篷船从老大桥“吱吱呀呀”划起,载着几个朋友顺江而下。我则在尤溪渡口恭候,小舟渐渐靠岸,拱手再三相迎。
诸位朋友皆青布长衫,古意盎然,立船头如玉树临风,携一描红鎏金食盒;食盒有三层,内有各色卤味,鸡鸭鱼肉一应俱全。
大热天的,还有一包猪头肉用鲜荷叶包着,显然都是些嗜好肥醇之徒。
我赶紧拿出好酒一瓶,五城米酒一坛……
正穿越着欲罢不能,手机响起。朋友发来信息,邀我小聚。
临近饭点请吃,似为不够诚恳;我则大喜过望,以为雪中送炭,屁颠颠急吼吼地出门吃请去了。
饭后回家,乘兴再写一段。
很多时候还是“画饼充饥”。写着写着,文字里描叙着美好,口腔里却愈发不可抑制地湿润起来,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此时五城茶干最应急。咸香鲜美,细腻柔韧,仅0.3厘米薄却折而不断。屯溪有的菜场里可买到正宗的,用冷开水焯一焯,细嚼慢咽三五块,足以阶段性地忘却一切美味佳肴。
遗憾的是,当年有虾米、笋丁、火腿丁的那种茶干,今天再也吃不到了。
画饼,却又不可得,往往想象力最丰富,心驰神往,文思翩然。
一起参与的还有休宁的一位老朋友,人长得帅,声音好听,富于磁性。他对文章的理解把握与我不谋而合。由他亲自来朗读,实在是更上一层楼的再创作。
视频更是美不胜收,为了好的视觉效果,这“一桌菜”都是现做现拍,画面清新,活色生香。
这些平台带来了相当可观的阅读量,仅新华网,就逾一千万。
我当然都转发的,一篇数次地刷存在感,“连累”朋友们也跟着数次点赞。
这一年,真有滋有味。
窗外,雪花飘飘,北风呼啸,天地一片苍茫。
案几上,几枝剪来的腊梅斜插在花瓶里,暗香浮动,氤氲满屋。
梅开二度,码字一年,吃喝文章,结集为《有滋有味》。
计有二十篇。水陆杂陈,荤素搭配,其实就是一桌菜:休宁状元宴。名头说来很大,如今也是家常菜肴,民间烟火;真要诉诸文字,还是有些“压力山大”,诚惶诚恐:这舌尖上的休宁,原本是滋味无穷的,落到我的笔下,可不要味同嚼蜡了!
家乡的事情,可一点马虎不得。
要做的一是重启记忆,一同唤起的还有暖暖的亲情,袅袅的乡愁;令人惊讶的是,当年的颊齿留芳,居然能绵延至今,回味无穷。
我难道天生是一个“好吃佬”?
二是寻访体验。去一道菜的发源地,探求其前世今生,品尝一下“原汁原味”(食材、佐料、烹饪方法等)。山水之间的行走,也变得趣味多多。有时,美食比美景更让人期许。
有了美景美食的加持,美文焉能不呼之欲出?
春江水暖,朋友送了几支璜尖大山里的春笋,我又在率水边的溪口镇肉铺沽得一方陈年火腿,于是就“腌笃鲜”起来。灶下文火,锅里“滴哚翻”(方言,水沸腾的样子),一会儿就香气袅袅,弥漫满屋。正在电脑前“噼里啪啦”地写《春山拔笋腌笃鲜》,怎挡得住厨房那边的诱惑?
于是就边写边吃。文章结尾,锅中物也去了大半。
据说梁启超先生的许多文章,是在麻将桌上口授而成的,且文采飞扬;在饼索万的一片碰撞中,大块头的社论文章若流水般汩汩而出。
接着蕨菜上市。于是就写《火腿蕨菜总相宜》,并且尽心尽力地做一道菜——火腿炒蕨菜。
取火腿心一小方,切成丝条状(适当有点肥的),先入锅爆炒,煸出油来,掐成寸把长的蕨菜全部扑入。始而热气腾腾,继而香气缭绕。待到八成熟时,撒入一把头刀的宽叶韭菜,然后几个上下,便可起锅装盘了。暗红、深褐、青绿,煞是好看。火腿之芳香、蕨菜之嫩爽、韭菜之鲜美,尽在口中。
春天是一个大快朵颐的季节,春天是一段文思汹涌的时光。半个月里,竟写出了五六篇,且与时令契合,决然不是“大棚菜”。屋里有花,插在粗瓷大口的腌菜坛里。先是金黄的油菜花,循序接上的是紫红的杜鹃花。皆是亲自采集而来,坛中花期一周左右,平添了几许野趣。
再放一曲:我自山中来,带着兰花草……缭梁绕室,袅袅飘忽。
其间,与几位休宁朋友去了齐云山下的南坑村,在油菜花海里流连忘返。醺然陶醉中,给这个美食专题命名《休宁·有滋有味》。
今年夏天奇热。窗帘拉紧,执一把芭蕉大蒲扇,轻摇慢拂,也顿生出缕缕凉意。赤膊上阵,心无旁骛,竟在一天里铺陈出七千余字,自己都惊讶不已。
足不出户,冰箱里只有馒头与榨菜矣!嘴里怕是淡出鸟来了。
黄昏,晚霞酡红如醉。开窗看新安江面如绿绸一样微微抖动;对岸则是葱郁的太阳山,山顶高耸着孙王阁。水边是尤溪古渡,有泊船的水埠头。
于是想象:一只竹篷船从老大桥“吱吱呀呀”划起,载着几个朋友顺江而下。我则在尤溪渡口恭候,小舟渐渐靠岸,拱手再三相迎。
诸位朋友皆青布长衫,古意盎然,立船头如玉树临风,携一描红鎏金食盒;食盒有三层,内有各色卤味,鸡鸭鱼肉一应俱全。
大热天的,还有一包猪头肉用鲜荷叶包着,显然都是些嗜好肥醇之徒。
我赶紧拿出好酒一瓶,五城米酒一坛……
正穿越着欲罢不能,手机响起。朋友发来信息,邀我小聚。
临近饭点请吃,似为不够诚恳;我则大喜过望,以为雪中送炭,屁颠颠急吼吼地出门吃请去了。
饭后回家,乘兴再写一段。
很多时候还是“画饼充饥”。写着写着,文字里描叙着美好,口腔里却愈发不可抑制地湿润起来,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此时五城茶干最应急。咸香鲜美,细腻柔韧,仅0.3厘米薄却折而不断。屯溪有的菜场里可买到正宗的,用冷开水焯一焯,细嚼慢咽三五块,足以阶段性地忘却一切美味佳肴。
遗憾的是,当年有虾米、笋丁、火腿丁的那种茶干,今天再也吃不到了。
画饼,却又不可得,往往想象力最丰富,心驰神往,文思翩然。
一起参与的还有休宁的一位老朋友,人长得帅,声音好听,富于磁性。他对文章的理解把握与我不谋而合。由他亲自来朗读,实在是更上一层楼的再创作。
视频更是美不胜收,为了好的视觉效果,这“一桌菜”都是现做现拍,画面清新,活色生香。
这些平台带来了相当可观的阅读量,仅新华网,就逾一千万。
我当然都转发的,一篇数次地刷存在感,“连累”朋友们也跟着数次点赞。
这一年,真有滋有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