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日期:
在节气里看见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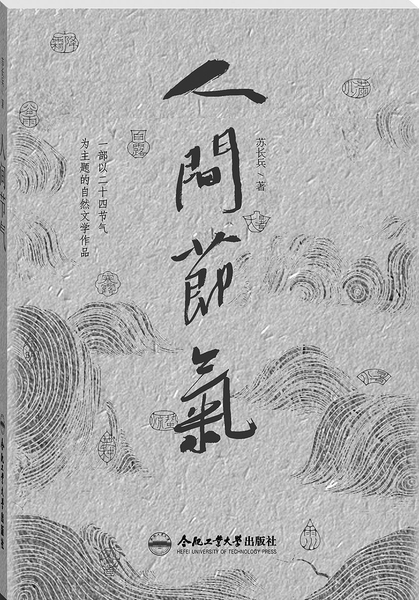
节气是中国文明的独特符码。远古时期,先民们只有模糊的时间概念,“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但对空间指向的“宇”和时间指向的“宙”却充满着未知而欲知的探索兴趣。就这样,“节气”这一带有浓烈的经验辩证、浪漫想象乃至朴素哲学色彩的时间概念,应运而生了。
传统中国社会的生根立命之本是农耕。农耕,即离不开与天时、地利的协应。虽然在“绝通天地”的隐喻诞生之后,对于天、地、人之间秩序的规定成了少数人的特权,但先民们出于生存的需要,自有其定义时空的智慧与法则:从春秋时期的仲春、仲夏、仲秋、仲冬之分,到战国时期《吕氏春秋》里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立冬、冬至等节气表述的出现,再到西汉淮南王刘安《淮南子》一书中“二十四个节气”概念的完整成型,可以说,节气是先民们对于四时轮转、物候迁移、万物生长最朴实也是最睿智的经验凝结。
长兵兄花了一年的多时间,以此时、此地、此情、此景的虔诚心境,与二十四节气相因应,写出了不一样的节气故事、节气文化,字里行间,浸润着对前人智慧的景仰,对乡村生活的回望,对传统文化的致敬乃至对人生态度的思考。无疑,《人间节气》是别致的,是深情的,也是意味隽永的。
在长兵兄的笔下,节气不仅仅是岁月的轮转,更浸润着最深沉的生活哲学。在节气的坐标系里,时间不再仅仅是时间,是自然界的法则,是“天人合一”的生动实践。
《人间节气》里一再品味与节气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各种农谚。当然,我也注意到,每每写及此处,长兵兄的笔触是最柔软的。循着农谚中节气指往的方向,他看到了家乡的稻麦,看到了儿时的时光,看到了远逝的亲人。节气,成了他内心深处与故乡形成隐秘连接的一扇暗门。节气依旧,农谚依旧,而曾经那个将节气、农谚常挂在嘴边的人,却再也回不来了。人生往往就是这样充满悖论。对于农村的孩子来说,一生的努力或许就是为了走出地理尺度的故乡,却永远走不出心灵尺度的故乡。在长兵兄柔软的文字里,寄寓着一个漂泊的游子对于故乡、对于亲情、对于古老文明投去的深情一瞥。
好在,人间烟火,世事沧桑,总抵不过中国人内在的浪漫。透过长兵兄旁征博引、不吝笔墨的丰富勾描,我们还能从节气里看到许多世俗尘烟之外的人间面相。从《诗经》开始,先民们就在歌咏“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就在感叹“七月鸣
,八月载绩”;而到了唐宋诗词家的笔下,节气又衍化为一种闲适、一种豁达、一种生命体验,于是便有了“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般对平淡美好生活的期许,有了“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恬静安然,有了“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的眷恋,自然,也少不了“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的淡淡哀伤。
这或许是一份专属于中国人的特有浪漫。细细品咂,其间又不免蕴藏着某种人生哲学,某些生活智慧。事实上,从中外思想史的视角来看,人类的哲思,多由自然物开启,且多包含着对时间这一重要生命尺度的把握,比如水与时间的关系。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曾说过,“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而与之殊途同归的,莫过于孔老夫子发出的“逝者如斯夫”的千古之叹。作为时间重要标识刻度的节气,更是如此。对于帝王将相而言,节气或许是他们自我标榜、自我展演、自我感动的最佳仪式时间,但于普罗大众而言,节气不过是星移斗转,是人间草木,是人在万物变迁之中所感受到的寒来暑往、月满盈亏、沧海桑田……
长兵兄显然对此深有体悟。《人间节气》写的是节气,但又未仅止步于节气,而更多写的是节气背后的人,人的生活,人的情趣,人的态度。比如,在写到“小满”时,他颇有感触地写道,“在二十四节气中,大小对称的节气有三对:小雪与大雪、小暑与大暑、小寒与大寒,唯有小满而没有‘大满’。”这难道是古人的疏忽吗?显然不是!至此,文章突然宕开一笔,笔调深沉:
人的一生,不满,则空留遗憾;过满,则招致损失。“小得盈满”,这不是最好的状态吗?欧阳修在《五绝·小满》诗里这样写道:“夜莺啼绿柳,皓月醒长空。最爱垄头麦,迎风笑落红。”世间的一切,不就正如小满时节田垄间迎风的麦子吗?小满,则傲立风中;大满,则凋零落地。这或许正是小满这个节气给予我们的人生智慧。
此般理性的思考,在《人间节气》中触目可及。如长兵兄所示,人在自然之中发现了节气的秘密,又在节气之中发现了人生的真谛。某种意义上说,中国人的很多哲学之思、人生境界,或许不过是节气轮转的一种思辨映射。
四时有序,岁月不居。在机器、科技、工业化逐渐成为人类生活底层座架的当下,品味节气,回望故乡,向传统文明致敬,有着一种令人动容的凝重感,但也往往予人以力量,鉴往知来、心驰天地,何尝不是人生常态!
正如长兵兄在后记里写下的这一段文字:“每一个节气的更迭,都给了我们深深的期盼,也给了我们悄悄的惊喜。我们常常会在不经意间惊喜地发现,人间一切美好总能应期而至,而且还会如期重逢。如此,我们的生活有了四季,时间有了痕迹,生命有了轮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