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日期:
楚墓竹蓆:两千多年未变的编织工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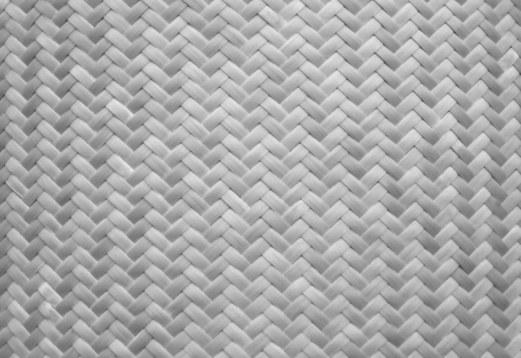
芮北海师傅编制的“人”字纹竹簟。

武王墩楚墓出土的竹蓆。

芮北海师傅在取竹。
在对楚墓进行考古发掘时,在填土层之下,一旦发掘到竹蓆,考古人员会产生一种兴奋,因为按照以往常例,楚墓竹蓆之下,就是棺椁了,而且,竹蓆的出现,往往是古墓没有被盗的标志。竹蓆,是楚墓棺椁之上的独特随葬器物,尤其是武王墩楚墓中出现的巨量竹蓆,再次引起人们的关注。
大量出土的“竹蓆”
楚墓椁盖板上覆盖竹蓆,是楚人特有的丧葬习俗,在楚墓发掘中屡见不鲜。到目前为止,淮南武王墩楚墓已出土竹蓆78条,总面积达200平米,这是前所未有的。竹蓆位于棺椁盖之上,以竹蓆为界,上面是填土,下面是椁室。按照椁室分区,围绕中间的棺室,东西南北四面各有两个分室,总共9室。东西南北与中间棺室五个平面单元,每个单元上为一张大竹蓆,即工作人员所说的“五张竹蓆,分别平铺在五大区域”。每个区域的竹蓆,没有编织上的联系。竹蓆总共4层,每层之间,也没有编织上的联系,是一层层累加的。
这些竹蓆是铺覆在椁盖板上的,竹蓆铺到椁盖板边缘之后,沿着椁盖板继续往下垂伸。椁盖板上的竹蓆,历经两千多年的承压,已经与椁盖板紧密粘贴在一起。椁盖板如果变形,粘在一起的竹蓆就随之变形,甚至断裂。竹蓆被厚厚的青膏泥包裹,两千多年来,一直处在弥封、与氧气隔绝的饱水状态。据目击者称,竹蓆刚露面时,仍然呈现新鲜的淡黄色。随着周边环境中的湿度、温度、含氧量发生变化,这些脆弱的随葬品会迅速被氧化、变形、变色。好在武王墩楚墓的竹蓆提取,采取了目前最为先进的薄荷醇临时固型技术,对刚露面的竹蓆进行临时加固处理。然后,再将已经加固的竹蓆紧急送往低氧实验室,加以保护。在这个过程中,粘附在竹蓆上的薄荷醇在空气中会自然挥发,不留残迹。但是,如果让薄荷醇一直自由挥发,竹蓆原有的水分也会迅速被蒸发,这会导致竹蓆干燥、起翘、变形、开裂,因此,经工作人员反复实验,通过加入酒精、加热等方法,终于找到既可以有效去除薄荷醇,又能确保竹蓆处于饱水状态的途径。
武王墩楚墓出土的竹蓆总量目前尚不确知,在低温实验室,其颜色显得发黑,但编织条缕清晰,为“人”字形编纹。经过对这批竹蓆碳14测年,判断其年代为公元前400年-公元前232年,与楚国都城迁至寿春(今安徽淮南寿县)的年代相一致。
工艺类似的“竹笥”
只要留意一下,人们会发现很多具有棺椁结构的楚墓中,都出土过另一种竹编之器——竹笥,它的出现位置与竹蓆不同。目前发现的墓中竹蓆,绝大部分都是覆盖在椁盖板上,少数棺椁底部也垫着竹蓆;竹笥则是放在椁室内,是用来盛放食物或衣物等的“竹箱子”。到目前为止,考古发现的楚国竹笥已达好几百件,它是当时楚人重要的生活用具。从形态上看,有正方形的,有长方形的,还有圆形的。据研究者统计,湖北江陵望山1号楚墓出土的8件竹笥为正方形;江陵拍马山39号楚墓出土的2件、马山1号楚墓出土的1件和湘乡牛形山2号楚墓出土的1件,都是圆形;其余出土的,均为长方形。后人有将圆形竹笥称作“箪”的,《孟子·梁惠王下》有“箪食壶浆,以迎王师”,是说用圆形的竹笥(箪)盛饭、用壶盛汤,来迎接自己拥戴的军队。这些造型不同的竹笥,表明楚人对竹编工艺的掌握已经十分娴熟,他们能够把竹材加工成需要的厚度,进行面状或者立体的编织,满足生产和生活需要。
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竹笥48其中装有食品的有中草药的8笥,装衣物及丝织品的6笥,装模型明器类的为4笥。
竹笥除了用来盛装食物、水果、农作物之外,还有的里面装着竹简。江陵天星观1号楚墓出土的竹简,就藏在竹笥内;湖南慈利石板村M36楚墓、湖北荆州秦家咀楚墓,均出土盛装竹简的竹笥。竹笥的这种用途,相当于后世的“书箱”。汉代以后,竹笥不仅是读书人的书箱,还是读书人的衣箱。
相比于竹蓆,竹笥形体面积小,编织工艺讲究、复杂,但二者编结的基本手法是一致的。另外,竹笥除了形制多样,还常常髹漆;竹蓆由于面积大,髹漆的,至今未见。
千年不变的编织工艺
楚国地域广阔,地貌多样,气候湿润。江汉地区漫山遍野都是竹子,对于当地居民而言,可谓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作为编制竹器的原材料,竹子可以用来编竹筐、竹篮、竹笥等生产、生活用品,而且竹制品干净,即便弄脏了,也容易清洗。竹器还富有弹性、韧性,坚固耐用。
截至目前,在安徽发现楚墓的地区主要有寿县、长丰、舒城、潜山和宣城。这些地区,处处生长翠竹,民间篾匠很多,编织技艺传承千年。
芜湖南陵县的弋江镇位于宣城与芜湖交界处的青弋江岸,是个古老的码头小镇,是皖南山区进入长江的门户。自古以来,皖南山区的土特产从黄山北麓,沿着青弋江,经由此地到芜湖,进入长江,上抵九江、武汉,下至南京、上海,因此,弋江镇成了皖南竹木集散地,不仅堆积着大量原竹木,还是竹木加工品的集散市场。
今年已经78岁的弋江镇老篾匠芮北海说,他的祖上几辈都是篾匠,稻箩、竹筐、竹篮、竹筛、簸箕、竹匾等,是当地百姓的日常用品。近年来,这些传统器具几乎都被皮革、尼龙、塑料制品取代了,传统竹器逐渐淡出了人们的生活圈,从而导致竹器行业的衰落。芮师傅说,过去镇上有几十家竹器店,篾匠上百人;如今只有两三家竹器店,手艺人只有三四个了,但农事之余,他的儿子芮时平和儿媳妇葛红莲都编制竹器。
芮师傅看了淮南武王墩楚墓发掘进展工作会影像资料回放后,对其中出土的竹蓆产生浓厚兴趣。他说,“人”字纹竹蓆的编织工艺,是现在篾匠普遍都掌握的,但没有人想到去突破,因为竹蓆多用在比较粗犷之处,没有必要作精细修饰,武王墩楚墓出土的竹蓆编织工艺,与现在篾匠编制的竹簟,没有什么两样。芮师傅惊叹道:“真的想不到,一种手工艺居然两千多年不变!”
芮师傅说,目前,当地居民夏天用的竹簟,仍然用这种工艺编制。这种竹簟也是当下竹器店销售的主要品种之一。芮师傅说,在篾匠掌握的编织技艺中,编制竹蓆的技艺,相对来说算简单的。竹蓆的尺幅一般较大,用场一般为不大讲究之处,例如屯条、竹篓、竹筐等,几乎都编成“人”字纹。形制小一些的,比如竹箱、竹扇、竹瓶等,不仅篾细,而且编织工艺也讲究一些,但这些工艺讲究的小型生活用竹器的编制,其边缘部分一般还是采用“人”字纹工艺作加固处理。芮师傅看到江陵太晖观50号楚墓出土的两件竹笥图片时,说这就是典型采用“人”字纹工艺加固边框的竹器。
芮师傅说,竹器用材分两种,一种是竹青,另一种是竹黄。竹青是竹子的表皮部分,因颜色青翠,故名。揭去竹青,“竹肉”部分颜色发黄,故名竹黄。竹青纤维比竹黄紧密,因此其韧性好,承受的拉力更大,用竹青编制的器物价格也明显高于竹黄产品。芮师傅说,从影像资料中,看不出武王墩出土的竹蓆是用竹青编制的,还是用竹黄编制的,但是,根据他的经验判断,应该是竹青,因为在江汉一带,竹子作为原材料是十分丰富的,不要说富贵如朝廷大官,就是家境一般的居民,也能用得起竹青产品。
芮师傅说,如果没有锐器破坏,用竹青编制的竹蓆抗拉和抗碾压性能是非常强的。如果编制之前,将竹青篾片蒸煮一下,那么,竹蓆不仅防腐,还防蛀虫,经久耐用。不要说覆盖在器物上不动,即便天天使用,细心的人家也能用上两代。楚墓棺椁上大量使用竹蓆,可能就是这个道理吧。
对楚墓中出土的一些回形、八边形、菱形纹饰的竹编器物,芮师傅啧啧称叹,他说:“这些竹器的编制,工艺上不仅涉及经纬篾垂直、斜交技法,还涉及以经纬篾绕骨架稀疏编织,从而形成各种中空花纹。还有的是围绕一个中心,向周边发散的圆形编织,这些编织技法,现在很多篾匠已经不做了,有的可能也做不出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