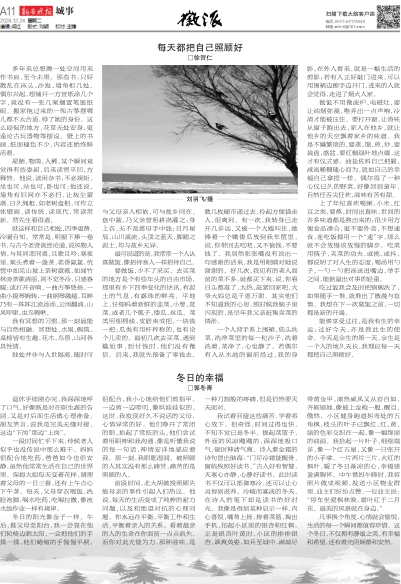发布日期:
每天都把自己照顾好
多年来总想腾一处空间用来作书房,至今未果。那些书,只好散乱在床头、沙发、墙角柜几处。偶尔兴起,想铺开一方宣纸涂几个字,竟没有一张几案搁置笔墨纸砚。搬家抱过来的一架古筝摆哪儿都不太合适,辱了她的身份。这么局促的地方,花草无处安身,更遑论古玩器物等摆设。壁上的书画,纸面褪色不少,内容还始终鲜活着。
屋陋,物简,人稀,某个瞬间竟觉得有些委屈,后来读贾平凹,方释然。他说,读闲杂书,不必规矩,坐也可,站也可,卧也可;他还说,墙角有旧网亦不必扫,让灰尘蒙落,日久绳粗,如老树盘根,可作立体壁画,读传统,读现代,常读常新。贾先生看得透。
就这样和自己相处,四季更替,冷暖自知。常常是,明窗下捧一卷书,与古今圣贤谈经论道,说风物人情,与其同悲同喜,且歌且吟;寒夜里,案头煮着一盏茶,茗香氤氲,恍惚中如见山坡上茶树葳蕤,如闻竹林旁茶歌清丽,则不觉冬冷,只感春暖;或打开音响,一曲古筝悠扬,一曲小提琴婉转,一曲钢琴激越,耳畔乃有一阵阵江流汤汤、云雨翻涌、山风呼啸、虫鸟啁啾。
我有冥想的习惯,那一刻最能与自然相融。冥想处,水果、碗筷、桌椅皆有生趣,花木、鸟兽、山河各具性情。
独处并非与人世隔离,随时可与父母亲人相依,可与故乡同在。盘中蔬,乃父亲曾躬耕浇灌之;身上衣,无不是慈母手中线;日月星辰,山川溪流,头顶之蓝天,脚踏之泥土,均与故乡无异。
最可说道的是,我常常一个人认真做饭,像招待客人一样招待自己。
要做饭,少不了采买。去买菜的地方是个有些年头的自由市场,那里有乡下四季变化的快讯,有泥土的气息,有露珠的鲜亮。平地上,仔细码着新鲜的韭菜、小葱、苋菜,或者几个瓠子、倭瓜、丝瓜。菜类用细棉线、皮筋束成把,一块钱一把;瓜类有用杆秤称的,也有论个儿卖的。最初几次去买菜,遇到尴尬事,到付钱时,他们没有微信。后来,我就先预备了零钱去,数几枚硬币递过去,拎起方便袋走人,很爽利。有一次,我转身已走开几步远,又被一个大嫂叫住,她捧着一个嫩倭瓜放到我车筐里,说,你带回去吃吧,又不值钱,不要钱了。我居然张张嘴没有说出一句感谢的话来,我是用眼睛对她说谢谢的。好几次,我见有的老人面前的菜不多,就都买下来,说,你看日头都毒了,太热,赶紧回家吧,大爷大妈总是千恩万谢。其实他们不知道我的心思,那时候我脑子里闪现的,是早年我父亲赶集卖菜的情形。
一个人背手系上围裙,低头洗菜,洗净菜里的每一粒沙子,洗着洗着,菜净了,心也静了。若偶尔有人从水池的窗前经过,我的身影,在外人看来,就是一幅生活的剪影;若有人正好敲门进来,可以用围裙边擦手边开门,进来的人就会觉得,走进了烟火人家。
做饭不用微波炉、电磁灶,要让油烟弥漫,唯弄出一点声响,冷清才能被压住。要打开窗,让香味从窗子跑出去,家人在他乡,就让他乡的天空飘着家乡的味道。我是不嫌繁琐的,要蒸、馏、煎、炒,要装盘、盛盆,要红椒绿叶地点缀,这才有仪式感。油盐佐料自己把握,咸淡稀稠随心而为,就如自己的幸福自己拿捏一样。偶尔得了一种心仪已久的野菜,好像回到童年,自然任舌尖狂欢,滋味有苦有甜。
上了年纪喜欢喝粥,小米、红豆之类,要熬,时间出真味,世间的许多味道都是熬出来的;很少用方便食品凑合,更不要外卖,不想速食,连吃饭都用一个“速”字,那么就不会放慢该放慢的脚步。吃菜用筷子,夹菜的功夫,或挑,或抖,都说明了对人生的态度;喝汤用勺子,一勺一勺把汤送进嘴边,举手之间,能掂量出对事的轻重。
吃过饭我会及时把锅碗洗了,如果随手一堆,就堆出了散漫与怠惰。我想在下一次做饭之前,一切都是新的开端。
能够享受过往,是我有生的幸运;过好今天,亦是我此生的使命。今天是余生的第一天,余生是一个人的地久天长,我理应每一天都把自己照顾好。
屋陋,物简,人稀,某个瞬间竟觉得有些委屈,后来读贾平凹,方释然。他说,读闲杂书,不必规矩,坐也可,站也可,卧也可;他还说,墙角有旧网亦不必扫,让灰尘蒙落,日久绳粗,如老树盘根,可作立体壁画,读传统,读现代,常读常新。贾先生看得透。
就这样和自己相处,四季更替,冷暖自知。常常是,明窗下捧一卷书,与古今圣贤谈经论道,说风物人情,与其同悲同喜,且歌且吟;寒夜里,案头煮着一盏茶,茗香氤氲,恍惚中如见山坡上茶树葳蕤,如闻竹林旁茶歌清丽,则不觉冬冷,只感春暖;或打开音响,一曲古筝悠扬,一曲小提琴婉转,一曲钢琴激越,耳畔乃有一阵阵江流汤汤、云雨翻涌、山风呼啸、虫鸟啁啾。
我有冥想的习惯,那一刻最能与自然相融。冥想处,水果、碗筷、桌椅皆有生趣,花木、鸟兽、山河各具性情。
独处并非与人世隔离,随时可与父母亲人相依,可与故乡同在。盘中蔬,乃父亲曾躬耕浇灌之;身上衣,无不是慈母手中线;日月星辰,山川溪流,头顶之蓝天,脚踏之泥土,均与故乡无异。
最可说道的是,我常常一个人认真做饭,像招待客人一样招待自己。
要做饭,少不了采买。去买菜的地方是个有些年头的自由市场,那里有乡下四季变化的快讯,有泥土的气息,有露珠的鲜亮。平地上,仔细码着新鲜的韭菜、小葱、苋菜,或者几个瓠子、倭瓜、丝瓜。菜类用细棉线、皮筋束成把,一块钱一把;瓜类有用杆秤称的,也有论个儿卖的。最初几次去买菜,遇到尴尬事,到付钱时,他们没有微信。后来,我就先预备了零钱去,数几枚硬币递过去,拎起方便袋走人,很爽利。有一次,我转身已走开几步远,又被一个大嫂叫住,她捧着一个嫩倭瓜放到我车筐里,说,你带回去吃吧,又不值钱,不要钱了。我居然张张嘴没有说出一句感谢的话来,我是用眼睛对她说谢谢的。好几次,我见有的老人面前的菜不多,就都买下来,说,你看日头都毒了,太热,赶紧回家吧,大爷大妈总是千恩万谢。其实他们不知道我的心思,那时候我脑子里闪现的,是早年我父亲赶集卖菜的情形。
一个人背手系上围裙,低头洗菜,洗净菜里的每一粒沙子,洗着洗着,菜净了,心也静了。若偶尔有人从水池的窗前经过,我的身影,在外人看来,就是一幅生活的剪影;若有人正好敲门进来,可以用围裙边擦手边开门,进来的人就会觉得,走进了烟火人家。
做饭不用微波炉、电磁灶,要让油烟弥漫,唯弄出一点声响,冷清才能被压住。要打开窗,让香味从窗子跑出去,家人在他乡,就让他乡的天空飘着家乡的味道。我是不嫌繁琐的,要蒸、馏、煎、炒,要装盘、盛盆,要红椒绿叶地点缀,这才有仪式感。油盐佐料自己把握,咸淡稀稠随心而为,就如自己的幸福自己拿捏一样。偶尔得了一种心仪已久的野菜,好像回到童年,自然任舌尖狂欢,滋味有苦有甜。
上了年纪喜欢喝粥,小米、红豆之类,要熬,时间出真味,世间的许多味道都是熬出来的;很少用方便食品凑合,更不要外卖,不想速食,连吃饭都用一个“速”字,那么就不会放慢该放慢的脚步。吃菜用筷子,夹菜的功夫,或挑,或抖,都说明了对人生的态度;喝汤用勺子,一勺一勺把汤送进嘴边,举手之间,能掂量出对事的轻重。
吃过饭我会及时把锅碗洗了,如果随手一堆,就堆出了散漫与怠惰。我想在下一次做饭之前,一切都是新的开端。
能够享受过往,是我有生的幸运;过好今天,亦是我此生的使命。今天是余生的第一天,余生是一个人的地久天长,我理应每一天都把自己照顾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