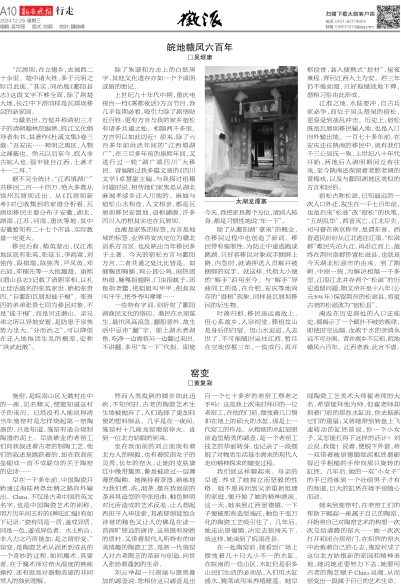发布日期:
皖地赣风六百年
“瓦屑坝,在立德乡,去城西二十余里。楚中诸大姓,多于元明之际自此徙。”其实,同治版《鄱阳县志》这段文字不够全面,除了荆楚大地,长江中下游同样是瓦屑坝移民的新家园。
与戴名世、方苞并称清初三才子的清朝翰林院编修、皖江文化倡导者朱书,其著作《杜溪文集》卷三载:“吾安庆……神明之奥区,人物之渊薮也。然元以后至今,皖人非古皖人也,强半徙自江西,土著才十一二耳。”
据不完全统计,“江西填湖广”共移民二百一十四万,绝大多数从饶州瓦屑坝迁出。从《瓦屑坝新考》对已收集到的家谱分析看,瓦屑坝移民主要分布于安徽、湖北、湖南、江苏、河南、重庆等地,其中安徽暂知有二十七个市县,实际数量一定更大。
移民后裔,精英辈出,仅江淮地区就有张英、张廷玉、李鸿章、刘铭传、段祺瑞、陈独秀、严凤英、邓石如、邓稼先等一大批翘楚。康熙《潜山县志》记载了清朝宰相、以礼让佳话盛名的张英家世,始祖张贵四,“自鄱阳瓦屑坝徙于桐”。张贵四的弟弟张贵七同为移民对象,不是“徙于桐”,而是另迁潜山。亲兄弟之所以异地安置,是防患于宗族势力坐大,“分而治之”,可以降低在迁入地抱团生乱的概率,史称“洪武赶散”。
除了族谱和方志上的白纸黑字,其他文化遗存亦如一个个或明或暗的胎记。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重庆电视台一档《雾都夜话》方言节目,我几乎每期必看,吸引力除了剧情贴近百姓,更有方言与我的家乡宿松有诸多共通之处。相隔两千多里,方言何以如此切近?原来,除了六百多年前洪武年间的“江西填湖广”,在三百多年前的康熙年间,又进行过一轮“湖广填四川”大移民。曾编辑过我多篇文章的《四川文学》卓慧副主编,与我探讨祖籍问题时说,相传她们家族是从湖北麻城孝感乡迁入川地的。麻城与宿松山水相连,人文相亲,都是瓦屑坝移民安置地,追根溯源,许多四川人的根其实也在瓦屑坝。
血液是家族的标签,方言是地域的标签,业界将安庆定位为赣北语系方言区,也反映出当年移民多于土著。今天的宿松方言与鄱阳方言,二者共通之处比比皆是。如脯胸即胸脯、鸡公即公鸡、闹热即热闹、腋嘎指翅膀、门虫指蚊子、团鱼指老鳖、把姐姐叫甲甲、把叔叔叫牙牙、把爷爷叫嗲嗲……
一些特有字词,则折射了鄱阳湖渔民文化的烙印。渔民在水里谋生,最怕风高浪急,翻船意外,故生活中忌讳“翻”字。船上湖水煮湖鱼,吃净一边需将另一边翻过来时,不讲翻,多用“车一下”代指。即使今天,我把家具挪个方位、请别人转身,都是习惯性地说“车一下”。
除了从鄱阳湖“拿来”的概念,在移民过程中也创造了新词。移民带有强制性,为防止中途逃跑或跳湖,只好将移民对象双手捆绑上路,内急时,就请押送人员解开被捆绑的双手。就这样,代指大小便的“解手”沿用至今。与“解手”异曲同工的是,在合肥、安庆等地尚存的“厝棺”现象,同样是瓦屑坝移民的衍生物。
叶落归根,移民虽远离故土,但心系故乡,入宗祠堂、葬祖坟山是身后的归宿。但山水迢迢,人去世了,不可能随时运往江西,暂且在空地停柩三年,一俟成行,再开棺捡骨,装入便携式“捡材”,星夜兼程,背回江西入土为安。若三年仍不能如愿,只好抱憾就地下葬,厝棺习俗由此形成。
江淮之地,水陆要冲,自古兵家必争,而位于吴头楚尾的宿松,更易受到战乱冲击。历史上,宿松既是瓦屑坝移民输入地,也是人口向外输出地。一百七十多年前,在安庆迁往陕南的移民中,就有我们千三公吴氏一族,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两地后人清明期间互有往来,至今陕南还保留着老腔老调的黄梅戏,以及与鄱阳湖地区类似的方言和民俗。
宿松古称松滋,已知最远的一次人口外迁,发生在一千七百年前,也是后来“松滋”改“宿松”的伏笔。“五胡乱华”,西晋灭亡,江北尽失,司马睿在南京称帝,是谓东晋。西晋遗民纷纷从江北逃往江南,“松滋郡”难民先泊九江,再沿江而上,最终在荆州南郡侨置松滋县,也就是今天湖北松滋市的由来。到了隋朝,中原一统,为解决相隔一千多里、江南江北并存两个“松滋”的历史遗留问题,隋文帝开皇十八年(公元598年)保留荆州的松滋县,将更古老的松滋改为“宿松县”。
淹没在历史深处的人口迁徙史,都揭示了一个颠扑不破的规律,即使时空远隔,血浓于水的亲情永远不可分割。背井离乡不忘祖,皖地赣风六百年。江西老表,此言不虚。
与戴名世、方苞并称清初三才子的清朝翰林院编修、皖江文化倡导者朱书,其著作《杜溪文集》卷三载:“吾安庆……神明之奥区,人物之渊薮也。然元以后至今,皖人非古皖人也,强半徙自江西,土著才十一二耳。”
据不完全统计,“江西填湖广”共移民二百一十四万,绝大多数从饶州瓦屑坝迁出。从《瓦屑坝新考》对已收集到的家谱分析看,瓦屑坝移民主要分布于安徽、湖北、湖南、江苏、河南、重庆等地,其中安徽暂知有二十七个市县,实际数量一定更大。
移民后裔,精英辈出,仅江淮地区就有张英、张廷玉、李鸿章、刘铭传、段祺瑞、陈独秀、严凤英、邓石如、邓稼先等一大批翘楚。康熙《潜山县志》记载了清朝宰相、以礼让佳话盛名的张英家世,始祖张贵四,“自鄱阳瓦屑坝徙于桐”。张贵四的弟弟张贵七同为移民对象,不是“徙于桐”,而是另迁潜山。亲兄弟之所以异地安置,是防患于宗族势力坐大,“分而治之”,可以降低在迁入地抱团生乱的概率,史称“洪武赶散”。
除了族谱和方志上的白纸黑字,其他文化遗存亦如一个个或明或暗的胎记。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重庆电视台一档《雾都夜话》方言节目,我几乎每期必看,吸引力除了剧情贴近百姓,更有方言与我的家乡宿松有诸多共通之处。相隔两千多里,方言何以如此切近?原来,除了六百多年前洪武年间的“江西填湖广”,在三百多年前的康熙年间,又进行过一轮“湖广填四川”大移民。曾编辑过我多篇文章的《四川文学》卓慧副主编,与我探讨祖籍问题时说,相传她们家族是从湖北麻城孝感乡迁入川地的。麻城与宿松山水相连,人文相亲,都是瓦屑坝移民安置地,追根溯源,许多四川人的根其实也在瓦屑坝。
血液是家族的标签,方言是地域的标签,业界将安庆定位为赣北语系方言区,也反映出当年移民多于土著。今天的宿松方言与鄱阳方言,二者共通之处比比皆是。如脯胸即胸脯、鸡公即公鸡、闹热即热闹、腋嘎指翅膀、门虫指蚊子、团鱼指老鳖、把姐姐叫甲甲、把叔叔叫牙牙、把爷爷叫嗲嗲……
一些特有字词,则折射了鄱阳湖渔民文化的烙印。渔民在水里谋生,最怕风高浪急,翻船意外,故生活中忌讳“翻”字。船上湖水煮湖鱼,吃净一边需将另一边翻过来时,不讲翻,多用“车一下”代指。即使今天,我把家具挪个方位、请别人转身,都是习惯性地说“车一下”。
除了从鄱阳湖“拿来”的概念,在移民过程中也创造了新词。移民带有强制性,为防止中途逃跑或跳湖,只好将移民对象双手捆绑上路,内急时,就请押送人员解开被捆绑的双手。就这样,代指大小便的“解手”沿用至今。与“解手”异曲同工的是,在合肥、安庆等地尚存的“厝棺”现象,同样是瓦屑坝移民的衍生物。
叶落归根,移民虽远离故土,但心系故乡,入宗祠堂、葬祖坟山是身后的归宿。但山水迢迢,人去世了,不可能随时运往江西,暂且在空地停柩三年,一俟成行,再开棺捡骨,装入便携式“捡材”,星夜兼程,背回江西入土为安。若三年仍不能如愿,只好抱憾就地下葬,厝棺习俗由此形成。
江淮之地,水陆要冲,自古兵家必争,而位于吴头楚尾的宿松,更易受到战乱冲击。历史上,宿松既是瓦屑坝移民输入地,也是人口向外输出地。一百七十多年前,在安庆迁往陕南的移民中,就有我们千三公吴氏一族,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两地后人清明期间互有往来,至今陕南还保留着老腔老调的黄梅戏,以及与鄱阳湖地区类似的方言和民俗。
宿松古称松滋,已知最远的一次人口外迁,发生在一千七百年前,也是后来“松滋”改“宿松”的伏笔。“五胡乱华”,西晋灭亡,江北尽失,司马睿在南京称帝,是谓东晋。西晋遗民纷纷从江北逃往江南,“松滋郡”难民先泊九江,再沿江而上,最终在荆州南郡侨置松滋县,也就是今天湖北松滋市的由来。到了隋朝,中原一统,为解决相隔一千多里、江南江北并存两个“松滋”的历史遗留问题,隋文帝开皇十八年(公元598年)保留荆州的松滋县,将更古老的松滋改为“宿松县”。
淹没在历史深处的人口迁徙史,都揭示了一个颠扑不破的规律,即使时空远隔,血浓于水的亲情永远不可分割。背井离乡不忘祖,皖地赣风六百年。江西老表,此言不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