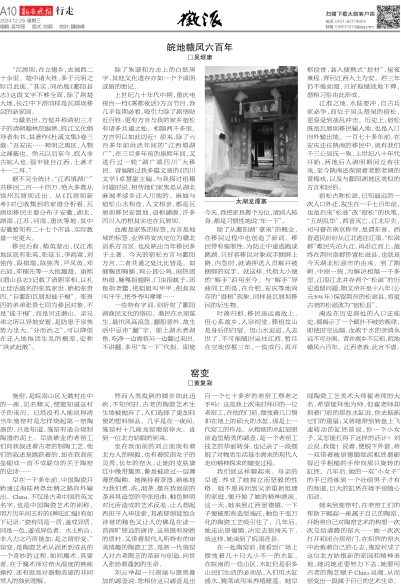发布日期:
窑变
施窑,是皖南山区无数村庄中的一座,见名释义,便能知道这村子的来历。已经没有人能说得清当年施窑村是怎样烧起第一窑陶器的,只是知道,施窑有适合烧制陶器的泥土。早就歇业的老窑工们向我叙述着古老的制陶工艺,他们的叙述是跳跃着的,却在我面前垒砌成一首不成联句的关于陶窑的史诗……
早在一千多年前,中国陶瓷开始通过海陆两条丝绸之路向外输出。China,不仅是古老中国的英文名字,也是中国陶瓷艺术的别称。明万历年间王圻的《稗史汇编》有如下记录:“瓷有同是一质,遂成异质,同是一色,遂成异色者。水土所合,非人力之巧所能加,是之谓窑变。”窑变,是陶瓷艺术从泥坯到成品的一个奇妙的过程,如同魔术,其要者,在于魔术师对窑火温度的熟练操控,还有就是对器物美感的非同常人的独到理解。
然而人类发展的脚步如此迅疾,不知何时,古老的陶瓷艺术生生地被抛弃了,人们选择了更加轻便的塑料制品。几乎是在一夜间,施窑村十几座龙窑熄窑停火。直到一位北方姑娘的到来。
坐在我面前的刘云面庞有着北方人的刚毅,也有着皖南女子的灵秀,长年的窑火,让她的皮肤黛红中微带黧黑,像是被涂过一层薄薄的陶釉。她操持着茶器,熟练地为我们煮、洗、沏茶,摆在我面前的茶具其造型的夸张扭曲,釉色鲜明对比所造成的艺术反差,让人想起西班牙人毕加索,其浓郁绵延饱含诗意的釉色又让人仿佛是在读一首深旷悠远的唐诗,这些既有原始的质朴,又带着现代人所特有的审美情趣的陶瓷工艺,是新一代施窑人对古老陶艺的革新与创造,向世人张扬着蓬勃的生命。
刘云举起一只深绿与黛黑叠加的滤壶说,您相信这只滤壶是出自一个七十多岁的老窑工蔡老之手吗?这是我上次来时拜识的一位老窑工,在他的门前,摆放着几口倒扣在地上的硕大的水缸,那是上一代窑工的作品。从粗硕的水缸到眼前造型精美的滤壶,是一个老窑工技艺的华丽转身,也记录了一段摆脱了对物质生活基本需求的现代人走向精神探求的嬗变过程。
我们就这样聊起来。母亲的早逝,养成了她独立而坚毅的性格。她不愿再回到父亲重新组建的家庭,便开始了她的精神漂流。这一天,她来到江西景德镇,一下子便被那些造型端庄,釉色千变万化的陶瓷工艺吸引住了。几年后,她走出景德镇,决定去独闯天下,就这样,她来到了皖南泾县。
在一处陶窑前,她看到广场上摆放着几十只大小不一的水缸。在皖南的一些山区,水缸仍是很多山民们生活的必须品,人们用水缸盛水、腌菜或用来养殖睡莲。她早闻陶瓷工艺美术大师翟老师的大名,希望能拜他为师,但翟老师却指着门前的那些水缸说,你去掂掂它们的重量;又将她带到转盘上飞速转动的缸坯前说,你一个小女子,又怎能扛得下这样的活计?刘云说,我能!说着,便脱下外套,将一双带着被景德镇细泥粗坯磨砺得近乎粗糙的手伸向那只旋转的缸坯。几年后,她的一双“小女子”的手已经练到一个壮硕男子才有的劲道,巨大的缸坯在她手里随心而动。
她来到施窑村,在老窑工们的帮助下砌起一座属于自己的陶窑,开始将自己对陶窑艺术的构想一次次交给沸腾的窑火……她一次次打开和闭合那窑门,在炽烈的窑火中冶炼着自己的心志,施窑村成了这位北方姑娘新的家园和精神圣地,她说她还要努力下去,她要用古老的陶艺赋予China灵魂,从而窑变出一段属于自己的艺术生命。
早在一千多年前,中国陶瓷开始通过海陆两条丝绸之路向外输出。China,不仅是古老中国的英文名字,也是中国陶瓷艺术的别称。明万历年间王圻的《稗史汇编》有如下记录:“瓷有同是一质,遂成异质,同是一色,遂成异色者。水土所合,非人力之巧所能加,是之谓窑变。”窑变,是陶瓷艺术从泥坯到成品的一个奇妙的过程,如同魔术,其要者,在于魔术师对窑火温度的熟练操控,还有就是对器物美感的非同常人的独到理解。
然而人类发展的脚步如此迅疾,不知何时,古老的陶瓷艺术生生地被抛弃了,人们选择了更加轻便的塑料制品。几乎是在一夜间,施窑村十几座龙窑熄窑停火。直到一位北方姑娘的到来。
坐在我面前的刘云面庞有着北方人的刚毅,也有着皖南女子的灵秀,长年的窑火,让她的皮肤黛红中微带黧黑,像是被涂过一层薄薄的陶釉。她操持着茶器,熟练地为我们煮、洗、沏茶,摆在我面前的茶具其造型的夸张扭曲,釉色鲜明对比所造成的艺术反差,让人想起西班牙人毕加索,其浓郁绵延饱含诗意的釉色又让人仿佛是在读一首深旷悠远的唐诗,这些既有原始的质朴,又带着现代人所特有的审美情趣的陶瓷工艺,是新一代施窑人对古老陶艺的革新与创造,向世人张扬着蓬勃的生命。
刘云举起一只深绿与黛黑叠加的滤壶说,您相信这只滤壶是出自一个七十多岁的老窑工蔡老之手吗?这是我上次来时拜识的一位老窑工,在他的门前,摆放着几口倒扣在地上的硕大的水缸,那是上一代窑工的作品。从粗硕的水缸到眼前造型精美的滤壶,是一个老窑工技艺的华丽转身,也记录了一段摆脱了对物质生活基本需求的现代人走向精神探求的嬗变过程。
我们就这样聊起来。母亲的早逝,养成了她独立而坚毅的性格。她不愿再回到父亲重新组建的家庭,便开始了她的精神漂流。这一天,她来到江西景德镇,一下子便被那些造型端庄,釉色千变万化的陶瓷工艺吸引住了。几年后,她走出景德镇,决定去独闯天下,就这样,她来到了皖南泾县。
在一处陶窑前,她看到广场上摆放着几十只大小不一的水缸。在皖南的一些山区,水缸仍是很多山民们生活的必须品,人们用水缸盛水、腌菜或用来养殖睡莲。她早闻陶瓷工艺美术大师翟老师的大名,希望能拜他为师,但翟老师却指着门前的那些水缸说,你去掂掂它们的重量;又将她带到转盘上飞速转动的缸坯前说,你一个小女子,又怎能扛得下这样的活计?刘云说,我能!说着,便脱下外套,将一双带着被景德镇细泥粗坯磨砺得近乎粗糙的手伸向那只旋转的缸坯。几年后,她的一双“小女子”的手已经练到一个壮硕男子才有的劲道,巨大的缸坯在她手里随心而动。
她来到施窑村,在老窑工们的帮助下砌起一座属于自己的陶窑,开始将自己对陶窑艺术的构想一次次交给沸腾的窑火……她一次次打开和闭合那窑门,在炽烈的窑火中冶炼着自己的心志,施窑村成了这位北方姑娘新的家园和精神圣地,她说她还要努力下去,她要用古老的陶艺赋予China灵魂,从而窑变出一段属于自己的艺术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