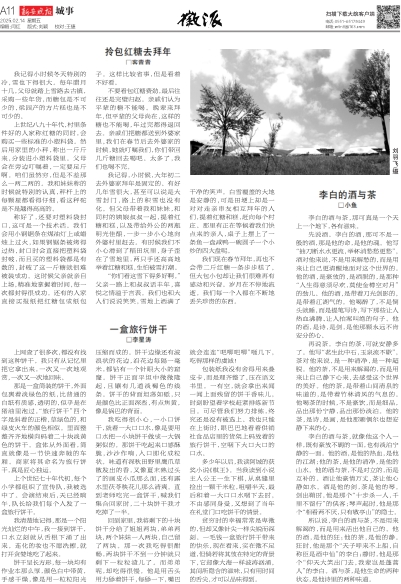发布日期:
拎包红糖去拜年
我记得小时候冬天特别的冷,雪也下得很大。每年腊月十几,父母就踏上雪路去古镇,采购一些年货,而糖包是不可少的,梁园产的方片糕也是不可少的。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村里条件好的人家称红糖的同时,会购买一些标准的小塑料袋。然后用家里的小秤,称出一斤斤来,分装进小塑料袋里。父母会在旁边叮嘱着,一定要足斤啊。咱们虽然穷,但是不差那么一两二两的。我和妹妹称的时候就特别的认真,秤杆上的每颗星都看得仔细,看这秤砣是不是翘得高高的。
称好了,还要对塑料袋封口,这可是一个技术活。我们会用小钢锯条在煤油灯上或蜡烛上过火,如果钢锯条被烤得过热,封口时会直接把塑料袋封破,而且买的塑料袋都是有数的,封破了这一斤糖就很难被装成功。这时候父亲就亲自上场,精准地掌握着时间,每一次都封得很成功。还有的人家直接买报纸把红糖包成纸包子。这样比较省事,但是看着不好看。
不要看包红糖费劲,最后往往还是完璧归赵。亲戚们认为平辈的糖不能喝。晚辈来拜年,但平辈的父母尚在,这样的糖也不能喝,年过完都得退回去。亲戚们把糖都送到外婆家里,我们在春节后去外婆家的时候,她就叮嘱我们,你们带回几斤糖回去喝吧。太多了,我们也喝不完。
我记得,小时候,大年初二去外婆家拜年是固定的。有好几年雪很大,甚至可以说是大雪封门,路上的积雪也没有化。但父母带着我和妹妹,和同村的姨娘叔叔一起,提着红糖和糕,以及带给外公的两瓶明光佳酿,一步一步小心地向外婆村里赶去。有时候我们不小心滑到了稻田坑里,身子歪在了雪地里,两只手还高高地举着红糖和糕,生怕被雪打潮。
“你们看这雪下得多好啊。”父亲一路上和叔叔话丰年,喜悦之情溢于言表。我们也和大人们说说笑笑,雪地上洒满了干净的笑声。白雪覆盖的大地是安静的,可是田埂上却是一对对走亲串友相互拜年的人们,提着红糖和糕,赶向每个村庄。那里有正在等候着我们快点来的亲人,桌子上摆上了一条鱼一盘咸鸭一碗圆子一个小炒的四大盘呢。
我们现在春节拜年,再也不会带二斤红糖一条步步糕了,但大包小包却让我们很难再有感动和兴奋。岁月在不停地流逝。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不断地丢失珍贵的东西。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村里条件好的人家称红糖的同时,会购买一些标准的小塑料袋。然后用家里的小秤,称出一斤斤来,分装进小塑料袋里。父母会在旁边叮嘱着,一定要足斤啊。咱们虽然穷,但是不差那么一两二两的。我和妹妹称的时候就特别的认真,秤杆上的每颗星都看得仔细,看这秤砣是不是翘得高高的。
称好了,还要对塑料袋封口,这可是一个技术活。我们会用小钢锯条在煤油灯上或蜡烛上过火,如果钢锯条被烤得过热,封口时会直接把塑料袋封破,而且买的塑料袋都是有数的,封破了这一斤糖就很难被装成功。这时候父亲就亲自上场,精准地掌握着时间,每一次都封得很成功。还有的人家直接买报纸把红糖包成纸包子。这样比较省事,但是看着不好看。
不要看包红糖费劲,最后往往还是完璧归赵。亲戚们认为平辈的糖不能喝。晚辈来拜年,但平辈的父母尚在,这样的糖也不能喝,年过完都得退回去。亲戚们把糖都送到外婆家里,我们在春节后去外婆家的时候,她就叮嘱我们,你们带回几斤糖回去喝吧。太多了,我们也喝不完。
我记得,小时候,大年初二去外婆家拜年是固定的。有好几年雪很大,甚至可以说是大雪封门,路上的积雪也没有化。但父母带着我和妹妹,和同村的姨娘叔叔一起,提着红糖和糕,以及带给外公的两瓶明光佳酿,一步一步小心地向外婆村里赶去。有时候我们不小心滑到了稻田坑里,身子歪在了雪地里,两只手还高高地举着红糖和糕,生怕被雪打潮。
“你们看这雪下得多好啊。”父亲一路上和叔叔话丰年,喜悦之情溢于言表。我们也和大人们说说笑笑,雪地上洒满了干净的笑声。白雪覆盖的大地是安静的,可是田埂上却是一对对走亲串友相互拜年的人们,提着红糖和糕,赶向每个村庄。那里有正在等候着我们快点来的亲人,桌子上摆上了一条鱼一盘咸鸭一碗圆子一个小炒的四大盘呢。
我们现在春节拜年,再也不会带二斤红糖一条步步糕了,但大包小包却让我们很难再有感动和兴奋。岁月在不停地流逝。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不断地丢失珍贵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