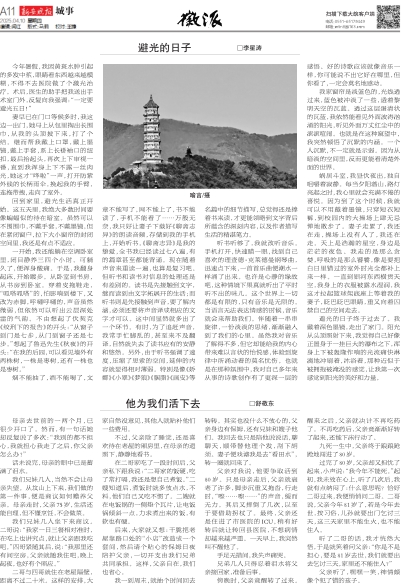发布日期:
避光的日子
今年暑假,我因黄斑水肿引起的多发中浆,眼睛看东西越来越模糊,不得不去医院做了个激光治疗。术后,医生的助手把我送出手术室门外,反复向我强调:“一定要避光五日!”
妻早已在门口等候多时,我这边一出门,她马上从包里掏出长围巾,从我的头顶披下来,打了个结。继而帮我戴上口罩,戴上墨镜,戴上手套,系上长褂袖口的纽扣,最后抬起头,再次上下审视一番,直到我浑身上下不露一丝肉光,她这才“哗啦”一声,打开防紫外线的长柄雨伞,挽起我的手臂,连拖带拽,走向了室外。
回到家里,避光生活真正开始。这五天里,我绝大多数时间要像蝙蝠似的待在暗室。虽然可以不围围巾,不戴手套,不戴墨镜,但在紧闭窗户,拉下大小窗帘的封闭空间里,我还是有点不适应。
一开始,我还能躺在空调卧室里,闭目静养三四个小时。可躺久了,便浑身酸痛。于是,我翻身起床,开始踱步。从卧室到书房,从书房到卧室。穿着皮拖鞋走,“呱嗒呱嗒”的,怕影响到楼下,又改为赤脚,呼嗵呼嗵的,声音虽然微弱,但依然可以听出云层深处雷的气韵。不由想起了伏契克《绞刑下的报告》的开头:“从窗子到门是七步,从门到窗子还是七步。”想起了鲁迅先生《秋夜》的开头:“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
烟不能抽了,酒不能喝了,文章不能写了,网不能上了,书不能读了,手机不能看了……万般无奈,我只好让妻子下载好《聊斋志异》的朗读音频,存储到我的手机上,开始听书。《聊斋志异》是我的挚爱,全书我已经读过七八遍,有的篇章甚至都能背诵。现在随着声音来重读一遍,也算是复习吧。但听书和读书对信息的处理还是有差别的。读书是先接触到文字,继而读到由文字拓展开的生活;而听书则是先接触到声音,要了解内涵,必须还要将声音译成相应的文字才可以。这中间显然就多出了一个环节。有时,为了追赶声音,我常手忙脚乱的,甚至来不及翻译,自然就失去了读书应有的安静和悠然。另外,由于听书强调了速度,压缩了思索的空间,延伸的内容就显得相对薄弱。特别是像《娇娜》《小翠》《梦狼》《胭脂》《画皮》等名篇中的细节描写,总觉得还是捧着书来读,才更能领略到文字背后所蕴含的深刻内容,以及作者描写生活的精湛笔力。
听书听够了,我就改听音乐。手机打开,快速瞄一眼,找到自己喜欢的理查德·克莱德曼钢琴曲,迅速点下来,一首首乐曲便潮水一样涌了出来。也许是心静的缘故吧,这种情境下果真就听出了平时听不出的味儿。这个世界上一切都是有限的,只有音乐是无限的。当语言无法表达情感的时候,音乐就会来帮助我们。伴随着一串串旋律,一份淡淡的思绪,渐渐融入到了我们的心里。虽然我对音乐了解得不多,但它却能给我的内心带来难以言状的怡悦感,体验到旋律中所涌动着的莫名忧伤。也就是在那种氛围中,我对自己多年来从事的诗歌创作有了更深一层的感悟。好的诗歌应该就像音乐一样,你可能说不出它好在哪里,但你看了,一定会莫名地感动。
我家窗帘是淡蓝色的,光线透过来,蓝色被冲淡了一些,透着黎明天空的瓦蓝。透过这层蛋清状的瓦蓝,我依然能看见外面波涛汹涌的阳光,听见外面万丈红尘中的滚滚喧闹。也就是在这种窥望中,我突然顿悟了沉默的内涵。一个人沉默,不一定就是示弱。因为从暗淡的空间里,反而更能看清楚外面的世界。
蜗居斗室,我昼伏夜出,独自咀嚼着寂静。每当夕阳落山,路灯亮起之时,我心里就会充满不倦的喜悦。因为到了这个时候,我就可以不用戴着墨镜,只穿短衣短裤,到校园内的大操场上肆无忌惮地散步了。妻子走累了,我还在走,操场上没有人了,我还在走。天上是浩瀚的星空,身边是茫茫的夜色。我走的是那么贪婪,呼吸的是那么饕餮,像是要把白日里错过的室外时光全都补上来一样。一直到银河东西横贯天空,我身上的衣服被露水湿润,我这才拉起篮球架底座上等着我的妻子,眨巴眨巴眼睛,重又向着囚禁自己的空间走去。
避光的日子终于过去了。我戴着深色墨镜,走出了家门。阳光从头顶照射下来,我觉得自己好像正置身于一挂巨大的瀑布之下,浑身上下被轰隆作响的光流痛快淋漓地冲刷着,沐浴着,那种近似于被拥抱被淹没的感觉,让我第一次感觉到阳光的美好和力量。
妻早已在门口等候多时,我这边一出门,她马上从包里掏出长围巾,从我的头顶披下来,打了个结。继而帮我戴上口罩,戴上墨镜,戴上手套,系上长褂袖口的纽扣,最后抬起头,再次上下审视一番,直到我浑身上下不露一丝肉光,她这才“哗啦”一声,打开防紫外线的长柄雨伞,挽起我的手臂,连拖带拽,走向了室外。
回到家里,避光生活真正开始。这五天里,我绝大多数时间要像蝙蝠似的待在暗室。虽然可以不围围巾,不戴手套,不戴墨镜,但在紧闭窗户,拉下大小窗帘的封闭空间里,我还是有点不适应。
一开始,我还能躺在空调卧室里,闭目静养三四个小时。可躺久了,便浑身酸痛。于是,我翻身起床,开始踱步。从卧室到书房,从书房到卧室。穿着皮拖鞋走,“呱嗒呱嗒”的,怕影响到楼下,又改为赤脚,呼嗵呼嗵的,声音虽然微弱,但依然可以听出云层深处雷的气韵。不由想起了伏契克《绞刑下的报告》的开头:“从窗子到门是七步,从门到窗子还是七步。”想起了鲁迅先生《秋夜》的开头:“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
烟不能抽了,酒不能喝了,文章不能写了,网不能上了,书不能读了,手机不能看了……万般无奈,我只好让妻子下载好《聊斋志异》的朗读音频,存储到我的手机上,开始听书。《聊斋志异》是我的挚爱,全书我已经读过七八遍,有的篇章甚至都能背诵。现在随着声音来重读一遍,也算是复习吧。但听书和读书对信息的处理还是有差别的。读书是先接触到文字,继而读到由文字拓展开的生活;而听书则是先接触到声音,要了解内涵,必须还要将声音译成相应的文字才可以。这中间显然就多出了一个环节。有时,为了追赶声音,我常手忙脚乱的,甚至来不及翻译,自然就失去了读书应有的安静和悠然。另外,由于听书强调了速度,压缩了思索的空间,延伸的内容就显得相对薄弱。特别是像《娇娜》《小翠》《梦狼》《胭脂》《画皮》等名篇中的细节描写,总觉得还是捧着书来读,才更能领略到文字背后所蕴含的深刻内容,以及作者描写生活的精湛笔力。
听书听够了,我就改听音乐。手机打开,快速瞄一眼,找到自己喜欢的理查德·克莱德曼钢琴曲,迅速点下来,一首首乐曲便潮水一样涌了出来。也许是心静的缘故吧,这种情境下果真就听出了平时听不出的味儿。这个世界上一切都是有限的,只有音乐是无限的。当语言无法表达情感的时候,音乐就会来帮助我们。伴随着一串串旋律,一份淡淡的思绪,渐渐融入到了我们的心里。虽然我对音乐了解得不多,但它却能给我的内心带来难以言状的怡悦感,体验到旋律中所涌动着的莫名忧伤。也就是在那种氛围中,我对自己多年来从事的诗歌创作有了更深一层的感悟。好的诗歌应该就像音乐一样,你可能说不出它好在哪里,但你看了,一定会莫名地感动。
我家窗帘是淡蓝色的,光线透过来,蓝色被冲淡了一些,透着黎明天空的瓦蓝。透过这层蛋清状的瓦蓝,我依然能看见外面波涛汹涌的阳光,听见外面万丈红尘中的滚滚喧闹。也就是在这种窥望中,我突然顿悟了沉默的内涵。一个人沉默,不一定就是示弱。因为从暗淡的空间里,反而更能看清楚外面的世界。
蜗居斗室,我昼伏夜出,独自咀嚼着寂静。每当夕阳落山,路灯亮起之时,我心里就会充满不倦的喜悦。因为到了这个时候,我就可以不用戴着墨镜,只穿短衣短裤,到校园内的大操场上肆无忌惮地散步了。妻子走累了,我还在走,操场上没有人了,我还在走。天上是浩瀚的星空,身边是茫茫的夜色。我走的是那么贪婪,呼吸的是那么饕餮,像是要把白日里错过的室外时光全都补上来一样。一直到银河东西横贯天空,我身上的衣服被露水湿润,我这才拉起篮球架底座上等着我的妻子,眨巴眨巴眼睛,重又向着囚禁自己的空间走去。
避光的日子终于过去了。我戴着深色墨镜,走出了家门。阳光从头顶照射下来,我觉得自己好像正置身于一挂巨大的瀑布之下,浑身上下被轰隆作响的光流痛快淋漓地冲刷着,沐浴着,那种近似于被拥抱被淹没的感觉,让我第一次感觉到阳光的美好和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