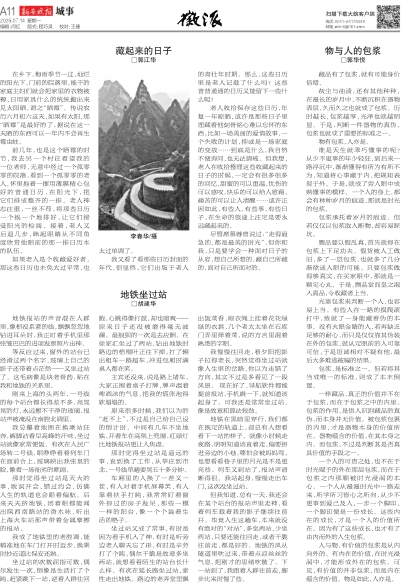发布日期:
地铁坐过站
地铁报站的声音混在人群里,像根没系紧的线,飘飘忽忽地钻进耳朵时,我正盯着手机里那张皱巴巴的进项发票照片出神。
等反应过来,窗外的站台已经滑过两个名字,玻璃上自己的影子还带着点茫然——又坐过站了。这毛病像是块老膏药,贴在我和地铁的关系里。
刚来上海的头两年,一号线的每个站台都长得差不多,亮晃晃的灯,永远擦不干净的玻璃,报站声被淹没在南腔北调里。
我总攥着地图在换乘站狂奔,裤脚沾着早高峰的汗味,坐过站就像家常便饭。有次在人民广场转二号线,眼睁睁看着列车门在面前合上,玻璃映出我张皇的脸,像看一场拙劣的默剧。
那时觉得坐过站是天大的事,耽误开会、错过约会,仿佛人生的轨道也会跟着偏航。后来天天挤地铁,闭着眼都能闻出陕西南路站的香水味,听出上海火车站那声带着金属摩擦的报站。
我成了地铁里的老腔调,能精准地在车门打开时迈步,换乘时抄近道比保安还熟。
坐过站的次数屈指可数,偶尔发生一次,倒像是生活打了个盹,赶紧跳下一站,逆着人群往回跑,心跳得像打鼓,却也暗爽——原来日子还没被磨得毫无波澜。最狼狈的一次是去应酬。在徐家汇坐过了两站,钻出地铁时路边的梧桐叶正往下掉,打了辆出租车一路超车,冲进包厢时满桌人都在笑。
主宾还没来,说是路上堵车,大家正围着桌子打牌,牌声混着啤酒沫的气息,把我的慌张泡得软塌塌的。
原来很多时候,我们以为的“赶不上”,不过是自己给自己设的倒计时。中间有几年不坐地铁,开着车在高架上兜圈,红绿灯比地铁报站更让人焦虑。
那时觉得坐过站是遥远的事,直到换了工作,从莘庄到市北,一号线单趟要晃五十多分钟。
车厢里的人换了一茬又一茬,有人对着手机屏幕笑,有人靠着扶手打盹,我常常盯着窗外掠过的房子发呆,那些一模一样的阳台,像一个个装着生活的格子。
坐过站又成了常事,有时是因为看手机入了神,有时是听旁边老人聊天忘了形,有时是辛劳打了个盹,偶尔干脆是故意多坐两站,就想看看陌生的站台长什么样。有次在延长路坐过站,索性走出地铁。路边的老弄堂里飘出饭菜香,晾衣绳上挂着花花绿绿的衣裳,几个老太太坐在石库门弄里择着菜,说的方言里混着熟悉的字眼。
我慢慢往回走,看夕阳把影子拉得老长,突然觉得坐过站就像人生里的岔路,你以为走错了方向,其实不过是多看见了一段风景。现在好了,导航软件都能提前报站,手机震一下,就知道该起身了。可我还是常常坐过站,像是故意和算法较劲。
地铁在黑暗里穿行,我们都在既定的轨道上,却总有人想看看下一站的样子。就像小时候走夜路,明明知道该直着走,偏要拐进旁边的小巷,哪怕会被妈妈骂,也想看看巷子里的月光是不是更亮些。列车又到站了,报站声清晰得很。我站起身,慢慢走出车门,这次没坐过站。
但我知道,总有一天,我还会在某个站台的报站声里走神,看着列车载着我的影子继续往前开。毕竟人生这趟车,本来就没有绝对的“对站”,多坐两站,少坐两站,只要还能往回走,或者干脆往前走,都是好的。地铁的风从隧道里吹过来,带着点凉丝丝的气息,把刚才的思绪吹散了。下一站到了,我跟着人群往前走,脚步比来时慢了些。
等反应过来,窗外的站台已经滑过两个名字,玻璃上自己的影子还带着点茫然——又坐过站了。这毛病像是块老膏药,贴在我和地铁的关系里。
刚来上海的头两年,一号线的每个站台都长得差不多,亮晃晃的灯,永远擦不干净的玻璃,报站声被淹没在南腔北调里。
我总攥着地图在换乘站狂奔,裤脚沾着早高峰的汗味,坐过站就像家常便饭。有次在人民广场转二号线,眼睁睁看着列车门在面前合上,玻璃映出我张皇的脸,像看一场拙劣的默剧。
那时觉得坐过站是天大的事,耽误开会、错过约会,仿佛人生的轨道也会跟着偏航。后来天天挤地铁,闭着眼都能闻出陕西南路站的香水味,听出上海火车站那声带着金属摩擦的报站。
我成了地铁里的老腔调,能精准地在车门打开时迈步,换乘时抄近道比保安还熟。
坐过站的次数屈指可数,偶尔发生一次,倒像是生活打了个盹,赶紧跳下一站,逆着人群往回跑,心跳得像打鼓,却也暗爽——原来日子还没被磨得毫无波澜。最狼狈的一次是去应酬。在徐家汇坐过了两站,钻出地铁时路边的梧桐叶正往下掉,打了辆出租车一路超车,冲进包厢时满桌人都在笑。
主宾还没来,说是路上堵车,大家正围着桌子打牌,牌声混着啤酒沫的气息,把我的慌张泡得软塌塌的。
原来很多时候,我们以为的“赶不上”,不过是自己给自己设的倒计时。中间有几年不坐地铁,开着车在高架上兜圈,红绿灯比地铁报站更让人焦虑。
那时觉得坐过站是遥远的事,直到换了工作,从莘庄到市北,一号线单趟要晃五十多分钟。
车厢里的人换了一茬又一茬,有人对着手机屏幕笑,有人靠着扶手打盹,我常常盯着窗外掠过的房子发呆,那些一模一样的阳台,像一个个装着生活的格子。
坐过站又成了常事,有时是因为看手机入了神,有时是听旁边老人聊天忘了形,有时是辛劳打了个盹,偶尔干脆是故意多坐两站,就想看看陌生的站台长什么样。有次在延长路坐过站,索性走出地铁。路边的老弄堂里飘出饭菜香,晾衣绳上挂着花花绿绿的衣裳,几个老太太坐在石库门弄里择着菜,说的方言里混着熟悉的字眼。
我慢慢往回走,看夕阳把影子拉得老长,突然觉得坐过站就像人生里的岔路,你以为走错了方向,其实不过是多看见了一段风景。现在好了,导航软件都能提前报站,手机震一下,就知道该起身了。可我还是常常坐过站,像是故意和算法较劲。
地铁在黑暗里穿行,我们都在既定的轨道上,却总有人想看看下一站的样子。就像小时候走夜路,明明知道该直着走,偏要拐进旁边的小巷,哪怕会被妈妈骂,也想看看巷子里的月光是不是更亮些。列车又到站了,报站声清晰得很。我站起身,慢慢走出车门,这次没坐过站。
但我知道,总有一天,我还会在某个站台的报站声里走神,看着列车载着我的影子继续往前开。毕竟人生这趟车,本来就没有绝对的“对站”,多坐两站,少坐两站,只要还能往回走,或者干脆往前走,都是好的。地铁的风从隧道里吹过来,带着点凉丝丝的气息,把刚才的思绪吹散了。下一站到了,我跟着人群往前走,脚步比来时慢了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