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日期:
用自己的眼光重新发现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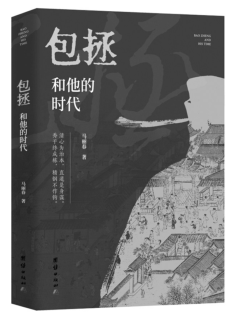

在近日首发的新书《包拯和他的时代》里,作家马丽春投注了她的文学热情和不竭的好奇心。面对被虚虚实实的文字架空的著名历史人物,马丽春的写作“金线”是“大事不虚”。放眼包拯所处的时代,走到历史文献的细节深处,“希望通过我的发现能够还原包拯真实的人生。”
用“问题意识”推动写作
徽派:马老师好,回到您熟悉的徽派。这一次是因为您的这本书而来:《包拯和他的时代》。对于这样一个大家熟知的历史人物,您这一次在书写的时候开辟了什么样的独特赛道?
马丽春:这本书从大历史角度来呈现包拯精彩的一生。之前很多包公书,虽然写的是包拯,可很多内容是虚构的,还夹杂有大量民间传说,和真实的包拯是两回事。包括现在影视剧、舞台剧中的包公戏,也以虚构为主。这本书就尽可能地还原真实的包公。当然,也不是每个字每句话皆有来历,事实上也无法做到,毕竟是历史人物,但书中所有重大的事件是真实的,这种写作叫“大事不虚”,而在小事上、细节上就会用上文学写法,这叫“小事可虚”。在文史写作上,从古至今,最通行的也是这个模式。像司马迁的《史记》,也是这样。一本书要好看,要有满满的干货满足读者的好奇心,要以史实做骨干撑起来,还要有文学的描写夹杂其中。既真实又好看,还要有大视野。
徽派:您对真实的包拯有哪些好奇?
马丽春:市场上有很多书,离真实的包拯很遥远。比如包拯弹劾某位达官贵人,很多包公书只写包拯弹劾,而不及他人。这种写法,我称为“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这显然也不符合历史的真实。仔细阅读《续资治通鉴长编》就会发现,同一年里,同一事件会有很多人出来弹劾,而包拯又是什么时候出场的,最后这个事件又是怎么收尾的,包拯在其间起什么作用?这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观察和分析这一事件很有意思。这样子去写包拯更客观,角度也更多元。客观,多维度,去研究历史人物,而不是先入为主,这在历史写作中,尤其重要。有位学者说过,写历史,搞文史研究,一要有好奇心,二要充满热情,要有满满的热情投入,因为研究本身是很寂寞的,相对比较枯燥,要做很多很笨的琐碎工作。三是要有发现问题的能力。这三点,我在这本书的写作中,基本上也是这样做的。我去年写了32万字的《陈亮师友录》,今年也要出版,陈亮是南宋人,状元,学者,词人,思想家。而包公是北宋名臣。为写他们,这几年我读的书以历史书籍为主,学术性的书以前不太看,但现在喜欢看。现在我还喜欢读原始文献,做读书笔记,且一做就是几十万字。这在文史写作中作用很大。现在很多年轻的文史作家写得很好,像现在很红的马伯庸,他们对历史有一些新鲜的解读值得我们借鉴学习。
徽派:在这本书的写作中,是叙述方式重要还是角度重要?
马丽春:两者都重要,但角度更重要。语言文字是工具,如何去呈现,从哪个角度进入,这在一开始就要有这个意识。当然叙述的方式也很重要。我在某一天突然有感觉了,便一口气写下“引子”,这样,这本书的叙述方式便开始建立了。后面只需要有问题意识。在很多章节里,是问题意识在推动文本的写作。可以说,问题意识贯穿全书始终。比如包拯的十年守孝,怎么去呈现,仅仅只是孝吗?合肥的包公祠为何在包公死后第四年才出现?欧阳修为何要弹劾包拯?包拯人生中的恩师是谁?他又如何报答这位恩师?等等。这本书如果说与别的包公书有什么不一样,问题意识推动这本书的写作,可能是最大的不一样。
包拯其实是个“理工男”
徽派:对于包拯这个人物,在书写他的时候,有什么新发现吗?
马丽春:我刚来到合肥的时候,就住在包公祠的对面。我在合肥最早认识的河流是包河,最吸引我的风景就是包河中的荷。那时我无数次穿行于包公祠,对庙里面塑的包公像,我有敬畏心但却没有亲近感。恐怕很多人都如此,因为我们对他了解都甚少。当有编辑邀我写包公时,我对编辑说,我感兴趣的只是这个真实的人物。而且,我对这个人物的写作不预设立场。也就是说,真正开始研究和写作,是靠好奇心和问题意识推着走的。这样,一步步去走近他,感受他。文史写作和新闻写作有相像处,和我原来的医生思维也有关联。医生很强调逻辑思维、整体观念和问题意识。这对写历史人物尤有帮助。
徽派:包拯现有的资料能满足到您的研究吗?
马丽春:北宋很多名臣,像范仲淹、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苏东坡这些人,都留下大量的文献资料,像苏东坡的文集里啥都有,有诗词歌赋,有书信手札题跋,有文章策论,还有很多疏文。欧阳修的文集里也是这样,内容极其丰富,像欧阳修弹劾包拯的疏文就留在他的文集里面。而包拯,却只留下170多篇奏折和一首诗,加上1973年出土的墓志铭,当然还有宋史本传和宋人笔记。要写包拯,这些资料是不够的。关于他自己早年的历史,他只说了八个字“生于草茅,蚤从宦学”。材料如此匮乏,那怎能写好他呢?我当时就想,找找他的同龄人吧,或许有惊喜的发现。我以上下二十年做一个区分,比包拯大20岁,比包拯小20岁,这些人留下来的文献,对写包拯应该是有帮助的,因为都是一个大时代的人。所以就买了这些人的书来看。果然别有洞天,后来在写作时派上了用场。这本书的前面一部分有些闲篇,但这些闲篇对认识那个时代,对认识包拯这个人,是很有帮助的。所以闲篇并不闲。比如,包拯青少年时期扑朔迷离,没有文字资料可以证明他的成长经历,而同时代的人因为科举制度,他们要读什么书,他们的仕宦生涯和成长经历,有很多共性的地方。表面上,是在文献资料极度匮乏之下,被逼采取的这么一种研究方法,从他们的人生来观照包拯的人生,这样去研究,倒也大大拓宽了角度,所以编辑后来为这本书定名为《包拯和他的时代》,倒也恰如其分。
徽派:北宋这样一个群星璀璨的年代,包拯是一个什么样独特的存在?
马丽春:包拯读书广博,孝顺父母,做事高效,极有章法,还很有创意。他的很多行为和思想吸引着我。说实话,写完了包拯,我对他的了解更深了一层。他在39岁左右才出山,在家里待了十年才出来,要按现在的话说,这样的进士哥有点傻。可他不一样。他在每一任内都留下闪光的政绩。我觉得包拯有理工男的特质,像欧阳修是典型的文科男,包拯看重的是做事,解决问题,而不是诗词歌赋。他不搞形式主义,几乎零社交。这些优点,恰恰也是我们时代所需要的。比如包拯在开封府尹任内做出两大革命性的举动:第一个是破除了门槛,拆除了“传达室”,让所有老百姓都可以直接面官,这一举动,史上所无;第二个,文件在他任内最为简约。他这种思想和做法是否让你感觉到亲切?包拯的与众不同成就了自己,也因此,他才成为“千年包公”。
新安晚报 安徽网 大皖新闻记者 吴华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