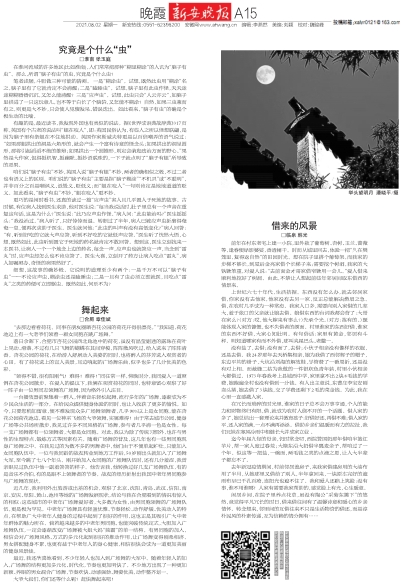发布日期:
借来的风景
□临泉韩光
前年在村东老宅上建一小院,里外栽了葡萄树、杏树、玉兰、蔷薇等,逢春便绿影婆娑,香透阑干。时而从城里回去,体验一把“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的田园时光。想在院子里搭个葡萄架,而我家的步梯不够长,到屋后金亮家借个长梯子来;需要挖个树洞,我家的大铁锨笨重,对爱人说:“去前面金才哥家借窄锨用一会儿。”爱人借来顺利地挖好了树洞。由此,不禁让人想起前些年邻居间取东借西的情景来。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生活拮据。东西没有怎么办,就去邻居家借,你家没有去他家,他家没有去另一家,反正总能解决燃眉之急。借,在农村几乎成为一种常态。我家人口多,需要向别人家借的几率大,羞于张口的父亲就让娘去借。娘借东西的台词我都会背了:大哥在家么?(对方:哎,他大婶来有事么?)先承个光。(对方:拣有的。)既能体现人家的慷慨,也不失借者的颜面。村里谁家的东西好借,谁家的东西不好借,大家心知肚明。有句俗话:家里有黄金,邻居有斗秤。明知道哪家有而不外借,那叫夹尾巴头、老鳖一。
没有盐了,去借;没有面了,去借;小伙子相亲没有像样的衣服,还是去借。我24岁那年去天桥集相亲,娘为我借了西邻辉子的帽子,东边平均的褂子,大坑沿刘海的解放鞋,尽管费了一番周折,还是没有对上相。而裁缝二姑为我做的一件银灰色青年装,村里小伙相亲大都借过。1973年春我考上县城西中学,家里拿不出2块8毛钱的学费,娘跑遍全村也没有借到一分钱。有人出主意说,东曹庄李宝安刚卖头猪,娘去借了3块钱,交了学费还剩下2毛的菜金钱。为此,我在心里一直感激人家。
在冗长而琐碎的时光里,谁家的日子总不会万事亨通,个人的能力和财物终归有限,借,就成为农村人绕不开的一个话题。借人家的多了,娘总结出一套理论来并教育孩子:好借好还,再借不难;借人家的平,还人家的满,一点不满再添添。借助乡亲们温暖而有力的拉扯,我们兄妹在寒风冷雨中相继长大并成家立业。
迄今年届九旬的母亲,仍时常念叨,西院赞国奶那年借咱半篮红芋片,帮一家人度过春荒;大塘东沿大奶借半瓢麦余子,帮咱过了一个年。似这等一把盐,一碗面,两毛钱之类的点滴之恩,让人大半辈子都忘不了。
去年新冠疫情期间,村前邻居盖房子,来我家借建房用的大油布用了半月,从她那里又借给了别人,半年拿回来,一块原本完好的遮雨布早已千孔百疮,连阳光也遮不住了。我和爱人还赔上笑脸:没有事,谁不用谁哪!人家有需要我家帮助的,感觉脸上有光,心生暖意。
闲居乡间,在院子里养点花草,虽没有陶公“采菊东篱下”的悠然,竟觉得平凡冗长的时日,借来借往间有了温馨诗意和暖心的乡亲情怀。转念想来,邻里间的互借往来不只是生活物资的借还,而是淳朴民风的朴素传递,互为信赖的情分拥有……
前年在村东老宅上建一小院,里外栽了葡萄树、杏树、玉兰、蔷薇等,逢春便绿影婆娑,香透阑干。时而从城里回去,体验一把“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的田园时光。想在院子里搭个葡萄架,而我家的步梯不够长,到屋后金亮家借个长梯子来;需要挖个树洞,我家的大铁锨笨重,对爱人说:“去前面金才哥家借窄锨用一会儿。”爱人借来顺利地挖好了树洞。由此,不禁让人想起前些年邻居间取东借西的情景来。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生活拮据。东西没有怎么办,就去邻居家借,你家没有去他家,他家没有去另一家,反正总能解决燃眉之急。借,在农村几乎成为一种常态。我家人口多,需要向别人家借的几率大,羞于张口的父亲就让娘去借。娘借东西的台词我都会背了:大哥在家么?(对方:哎,他大婶来有事么?)先承个光。(对方:拣有的。)既能体现人家的慷慨,也不失借者的颜面。村里谁家的东西好借,谁家的东西不好借,大家心知肚明。有句俗话:家里有黄金,邻居有斗秤。明知道哪家有而不外借,那叫夹尾巴头、老鳖一。
没有盐了,去借;没有面了,去借;小伙子相亲没有像样的衣服,还是去借。我24岁那年去天桥集相亲,娘为我借了西邻辉子的帽子,东边平均的褂子,大坑沿刘海的解放鞋,尽管费了一番周折,还是没有对上相。而裁缝二姑为我做的一件银灰色青年装,村里小伙相亲大都借过。1973年春我考上县城西中学,家里拿不出2块8毛钱的学费,娘跑遍全村也没有借到一分钱。有人出主意说,东曹庄李宝安刚卖头猪,娘去借了3块钱,交了学费还剩下2毛的菜金钱。为此,我在心里一直感激人家。
在冗长而琐碎的时光里,谁家的日子总不会万事亨通,个人的能力和财物终归有限,借,就成为农村人绕不开的一个话题。借人家的多了,娘总结出一套理论来并教育孩子:好借好还,再借不难;借人家的平,还人家的满,一点不满再添添。借助乡亲们温暖而有力的拉扯,我们兄妹在寒风冷雨中相继长大并成家立业。
迄今年届九旬的母亲,仍时常念叨,西院赞国奶那年借咱半篮红芋片,帮一家人度过春荒;大塘东沿大奶借半瓢麦余子,帮咱过了一个年。似这等一把盐,一碗面,两毛钱之类的点滴之恩,让人大半辈子都忘不了。
去年新冠疫情期间,村前邻居盖房子,来我家借建房用的大油布用了半月,从她那里又借给了别人,半年拿回来,一块原本完好的遮雨布早已千孔百疮,连阳光也遮不住了。我和爱人还赔上笑脸:没有事,谁不用谁哪!人家有需要我家帮助的,感觉脸上有光,心生暖意。
闲居乡间,在院子里养点花草,虽没有陶公“采菊东篱下”的悠然,竟觉得平凡冗长的时日,借来借往间有了温馨诗意和暖心的乡亲情怀。转念想来,邻里间的互借往来不只是生活物资的借还,而是淳朴民风的朴素传递,互为信赖的情分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