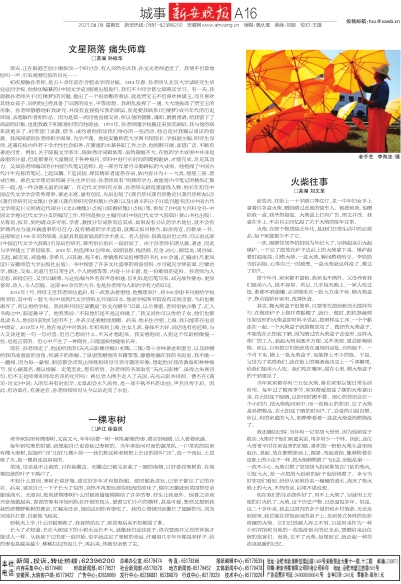发布日期:
文星陨落痛失师尊
□芜湖孙栋华
那天,正在殷港艺创小镇参加一个研讨会,有人突然告诉我,孙文光老师逝世了。我情不自禁地惊叫一声,引来周围吃惊的目光……
初次接触孙老师,是五十余年前在合肥求学的时候。1964年春,孙老师从北京大学读研究生毕业返回学校,他参加编纂的《中国文学史》刚刚出版发行,我们不少同学都立即购买学习。有一天,我请教孙老师关于《红楼梦》的问题,提出了一个很幼稚的看法,就是贾宝玉不但喜欢林黛玉,而且喜欢其他女孩子,说明他已经具备了早期的民主、平等思想。我胡乱发挥了一通,大大地拔高了贾宝玉的形象。孙老师静静地听我讲完,并没有直接指斥我的谬误,而是要我联系《红楼梦》成书年代的历史环境,去理解作者和作品。因为是第一次同他直接交谈,所以他的儒雅、谦和、循循善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使我敢于和愿意时常向他请益。1970年,孙老师随学校搬迁来到芜湖后,我与他的联系就更多了,时常登门求教,借书,或约请他指导我们举办的一些活动,他总是对我赐以周详的指教。我深深感到孙老师积学深厚,为学严谨。他是安徽师范大学图书馆馆长,学报副主编,研究生导师,还兼任校内外若干学术性社会职务,在繁重的本兼各职工作之余,他视野开阔,涉猎广泛,不断有著述问世。例如,关于陈毅文学系年、陈独秀诗词辑佚等,虽然篇幅不大,在他的学术成果中并非是最重的分量,但是都要在大量散见于各种报刊、资料中进行长时间的爬梳剔抉,才能完成,足见其功力。又如孙老师编印的《中国历代笔记选粹》,是一部穷年累月辛勤耕耘的大成果。他检阅了中国古代汗牛充栋的笔记,上起汉魏,下迄民国,择其精彩者逐条存录,依内容分为十一大类,煌煌三册,蔚成巨帙。著名文学理论家何满子先生评价说:孙老师具有“别择的学力,故能将古今笔记的精华汇集在一起,是一件功德无量的贡献”。在近代文学研究方面,孙老师无疑是重量级人物,他长年担任中国近代文学学会常务理事,著述丰富,屡有创见,先后出版了《龚自珍》《龚自珍散论》《龚自珍师友记》《龚自珍研究论文集》(合著)《龚自珍研究资料集》(合著)以及《清末四公子》《梁启超书话》《中国古代文学简史》(元明清近代部分)《北山楼集》(点校)《皖雅初集》(点校)等,参加了《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近代文学分支的编写工作,特别是独立主编完成《中国近代文学大辞典》(黄山书社出版),从筹划、拟目,到约请众多专家、学者、教授分写词条而总其成,如果没有公认的学术地位,就不会有罗致四方力量共襄盛事的号召力,没有精湛的学术造诣,就难以拟目精当、取舍得宜,而勒成一书。这部厚达1300多页的辞典,无疑具有最新最高的学术意义。有人曾说:辞典是后世之师,可以说这部《中国近代文学大辞典》引导后世研究,够用很长很长一段时间了。由于孙老师长期从教、著述,因此与学界建立了密切联系。2016年,他选择92位师友,如游国恩、钱昌照、巴金、冰心、顾廷龙、周谷城、王起、臧克家、郑逸梅、李希凡、冯其庸、程千帆、季镇淮和吴组缃等的书札100余通,汇编成《尺素风谊》(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书中保留了许多文化盛事的背景资料,亦可窥见学界前辈、巨擘治学、撰述、交友、论道乃至日常生活,个人情绪等等,内容十分丰富,是一份难得的史料。孙老师为人忠恕,深得信任,又学识渊博,与这些海内外名家声息相通,信札似是信笔写来,却无故作姿态,更加客观、动人,令人信服。这部400余页的大书,也是孙老师为人和治学有力的印证。
2014年7月,师母王世芸老师仙逝后,有一次我去看望他,他整理家什,将500余册书刊捐给学校图书馆,其中有一套大书《中国现代文学资料丛书》影印本,他说学校图书馆没有买到全套,今后也难凑齐了,所以捐给学校。我说图书馆应该镌刻“孙文光赠书”印章,以示尊重,否则很快分散了,汇入书海之中,踪迹难寻了。他笑笑说:“不知他们是不是这样做了。”我又说你可以传给子女,他们也都是读书人,他说目前他们还用不上,并表示还要继续捐赠。后来,他长住合肥、上海,我只能常在电话中请安。2019年8月,他在电话中对我说:年初来到上海,住女儿家,身体不太好,说话也有些迟顿,与人交谈还能一句一句对答,但自己想说什么,半天才想起来。我安慰他说,人到这个年龄稍微慢一些,也是正常的。但心中产生了一种隐忧,只能遥祝他健康长寿。
现在,孙老师走了,他送给我的《天光云影楼诗稿》(初集、二集)等十余种著述和墨宝,以及转赠给我的凌虚画的金鱼、何满子的条幅、丁景唐签赠他的书籍等等,静静地躺在我的书房里,我不敢一一翻阅,因为每一凝视,眼前都会浮现出师尊和师母可亲可敬的形象,想起他对我的教诲和种种细节,而心痛莫名,难以排解。走笔至此,忽有所悟。孙老师的书斋取名“天光云影楼”,虽得之朱熹诗句,但不正是师尊和师母名讳的化用吗?两位老人携手走入了天国,天光云影共徘徊。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说:人的年寿有时而尽,文章却会永久流传,是一项千秋不朽的功业,声名自传于后。因此,有诗章在,有著述在,孙老师和师母从今以后走向了永恒。
那天,正在殷港艺创小镇参加一个研讨会,有人突然告诉我,孙文光老师逝世了。我情不自禁地惊叫一声,引来周围吃惊的目光……
初次接触孙老师,是五十余年前在合肥求学的时候。1964年春,孙老师从北京大学读研究生毕业返回学校,他参加编纂的《中国文学史》刚刚出版发行,我们不少同学都立即购买学习。有一天,我请教孙老师关于《红楼梦》的问题,提出了一个很幼稚的看法,就是贾宝玉不但喜欢林黛玉,而且喜欢其他女孩子,说明他已经具备了早期的民主、平等思想。我胡乱发挥了一通,大大地拔高了贾宝玉的形象。孙老师静静地听我讲完,并没有直接指斥我的谬误,而是要我联系《红楼梦》成书年代的历史环境,去理解作者和作品。因为是第一次同他直接交谈,所以他的儒雅、谦和、循循善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使我敢于和愿意时常向他请益。1970年,孙老师随学校搬迁来到芜湖后,我与他的联系就更多了,时常登门求教,借书,或约请他指导我们举办的一些活动,他总是对我赐以周详的指教。我深深感到孙老师积学深厚,为学严谨。他是安徽师范大学图书馆馆长,学报副主编,研究生导师,还兼任校内外若干学术性社会职务,在繁重的本兼各职工作之余,他视野开阔,涉猎广泛,不断有著述问世。例如,关于陈毅文学系年、陈独秀诗词辑佚等,虽然篇幅不大,在他的学术成果中并非是最重的分量,但是都要在大量散见于各种报刊、资料中进行长时间的爬梳剔抉,才能完成,足见其功力。又如孙老师编印的《中国历代笔记选粹》,是一部穷年累月辛勤耕耘的大成果。他检阅了中国古代汗牛充栋的笔记,上起汉魏,下迄民国,择其精彩者逐条存录,依内容分为十一大类,煌煌三册,蔚成巨帙。著名文学理论家何满子先生评价说:孙老师具有“别择的学力,故能将古今笔记的精华汇集在一起,是一件功德无量的贡献”。在近代文学研究方面,孙老师无疑是重量级人物,他长年担任中国近代文学学会常务理事,著述丰富,屡有创见,先后出版了《龚自珍》《龚自珍散论》《龚自珍师友记》《龚自珍研究论文集》(合著)《龚自珍研究资料集》(合著)以及《清末四公子》《梁启超书话》《中国古代文学简史》(元明清近代部分)《北山楼集》(点校)《皖雅初集》(点校)等,参加了《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近代文学分支的编写工作,特别是独立主编完成《中国近代文学大辞典》(黄山书社出版),从筹划、拟目,到约请众多专家、学者、教授分写词条而总其成,如果没有公认的学术地位,就不会有罗致四方力量共襄盛事的号召力,没有精湛的学术造诣,就难以拟目精当、取舍得宜,而勒成一书。这部厚达1300多页的辞典,无疑具有最新最高的学术意义。有人曾说:辞典是后世之师,可以说这部《中国近代文学大辞典》引导后世研究,够用很长很长一段时间了。由于孙老师长期从教、著述,因此与学界建立了密切联系。2016年,他选择92位师友,如游国恩、钱昌照、巴金、冰心、顾廷龙、周谷城、王起、臧克家、郑逸梅、李希凡、冯其庸、程千帆、季镇淮和吴组缃等的书札100余通,汇编成《尺素风谊》(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书中保留了许多文化盛事的背景资料,亦可窥见学界前辈、巨擘治学、撰述、交友、论道乃至日常生活,个人情绪等等,内容十分丰富,是一份难得的史料。孙老师为人忠恕,深得信任,又学识渊博,与这些海内外名家声息相通,信札似是信笔写来,却无故作姿态,更加客观、动人,令人信服。这部400余页的大书,也是孙老师为人和治学有力的印证。
2014年7月,师母王世芸老师仙逝后,有一次我去看望他,他整理家什,将500余册书刊捐给学校图书馆,其中有一套大书《中国现代文学资料丛书》影印本,他说学校图书馆没有买到全套,今后也难凑齐了,所以捐给学校。我说图书馆应该镌刻“孙文光赠书”印章,以示尊重,否则很快分散了,汇入书海之中,踪迹难寻了。他笑笑说:“不知他们是不是这样做了。”我又说你可以传给子女,他们也都是读书人,他说目前他们还用不上,并表示还要继续捐赠。后来,他长住合肥、上海,我只能常在电话中请安。2019年8月,他在电话中对我说:年初来到上海,住女儿家,身体不太好,说话也有些迟顿,与人交谈还能一句一句对答,但自己想说什么,半天才想起来。我安慰他说,人到这个年龄稍微慢一些,也是正常的。但心中产生了一种隐忧,只能遥祝他健康长寿。
现在,孙老师走了,他送给我的《天光云影楼诗稿》(初集、二集)等十余种著述和墨宝,以及转赠给我的凌虚画的金鱼、何满子的条幅、丁景唐签赠他的书籍等等,静静地躺在我的书房里,我不敢一一翻阅,因为每一凝视,眼前都会浮现出师尊和师母可亲可敬的形象,想起他对我的教诲和种种细节,而心痛莫名,难以排解。走笔至此,忽有所悟。孙老师的书斋取名“天光云影楼”,虽得之朱熹诗句,但不正是师尊和师母名讳的化用吗?两位老人携手走入了天国,天光云影共徘徊。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说:人的年寿有时而尽,文章却会永久流传,是一项千秋不朽的功业,声名自传于后。因此,有诗章在,有著述在,孙老师和师母从今以后走向了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