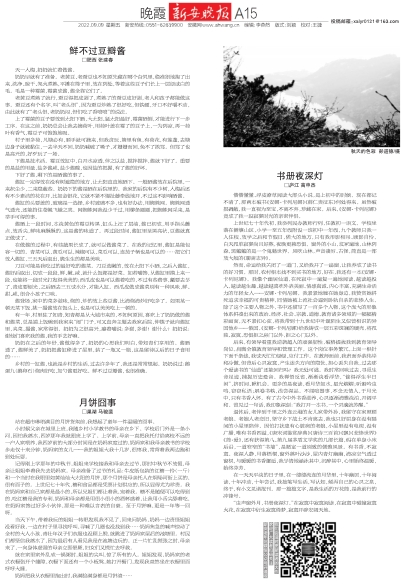发布日期:
书册夜深灯
□庐江高申杰
懵懵懂懂、浮皮潦草阅读大部头小说,是上初中的时候。现在都记不清了,那两本破书《安娜·卡列尼娜》《薛仁贵征东》何处得来。虽然破损凋敝,我一直视为至宝,不离不弃,珍藏在家。后来,《安娜·卡列尼娜》竟成了我一段寂寥时光的亲密伴侣。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忝列民办教师行列,任教初一语文。学校坐落在僻壤山区,小学一至五年级附设一班初中一年级,九个教师只我一人住校,放学之后和节假日,偌大的地方,只有我形影相吊、顾影自怜。白天孤单寂寥尚且好熬,夜晚更兼恐惧。窗外的小山,坟冢遍地,山林阴森,黑魆魆的是一个鬼魅世界。风吹山林,声音凄厉、古怪,简直是一部放大版的《聊斋志异》。
然而,命运给我关闭了一道门,又给我开了一扇窗,让我养成了读书的好习惯。那时,农村根本找不到买书的地方,好在,我还有一本《安娜·卡列尼娜》。我像个幽居仙道,在死寂中一遍复一遍地阅读,越读越投入,越读越生趣,越读越喜欢外表美丽、情感真诚、内心丰富、充满生命活力的年轻女人——安娜·卡列尼娜。我紧紧地缠在她身边,我赞赏她拼死追求幸福的可贵精神,同情她被上流社会逼到卧轨自杀的悲惨人生。除了这个主要人物之外,书中还描写了一百多个人物,这个庞大的形象体系拼凑出来的政治、经济、社会、宗教、道德、教育诸多领域的一幅幅精彩画面,无不紧扣心弦,将我带到十九世纪中叶既陌生又似曾相识的异国他乡——俄国。《安娜·卡列尼娜》给我铸成一层五彩斑斓的硬壳,将孤独、寂寞、恐惧拒之房门以外,拒之心门以外。
后来,有领导看重我逆袭超人的顽强韧性,破格提拔我到教育领导岗位,肩膺全镇教育领导和管理工作。这个岗位事务繁冗,上面一根针下面千条线,我成天忙忙碌碌,应付工作。在教师面前,我表面乔装伟岸和冷傲,但背后心灵寂寞,产生迷失方向的隐忧,担心丢失自我,过去那个爱读书的“仙道”还能回归吗?我无处可逃。我时常回味过去,寻觅生命足迹,捕捉历史跫音。我禅悟反省,渐渐淡看浮华,“偷得浮生半日闲”,挤时间、瞅机会。更多的是夜读,看月华如水,星光熠熠;听蛩吟虫鸣,窃窃私语;展卷书帙,浅尝深品。不闻喧嚣事,不念无情人,于月光中,只有书香入怀。有了古今中外书香滋养,心灵逐渐清雅淡泊,开阔平和。曾见过一句话,我印象深刻:“我打开一本书,一个灵魂就苏醒。”
退休后,老伴到千里之外连云港的女儿家带外孙,我留守在家照顾老娘。老娘人老恋旧,坚守乡下故土不肯离去,我也只好屈身在没有隔间的小屋里陪伴。因怕打扰患有心脏病的老娘,小屋里没有电视,没有广播,唯有书香四溢,《唐宋词鉴赏辞典》《唐诗三百首》《飘》《悲惨世界》《简·爱》,还有获得第八、第九届茅盾文学奖的几部长篇,码在单身小床后沿,一道窄窄的“书墙”,是陋室一道别致的儒雅风景。有书香,不寂寞。夜深人静,月落梧桐,窗外落叶沙沙,屋内青灯幽幽,清凉空气透过窗棂,与暖暖的书香邂逅,我尽情地涵泳其中,沉醉其中,心里始终温暖,始终芬芳。
在一天天平淡的日子里,在一缕缕流连的月华里,十年幽居,十年阅读,十年冲动,十年尝试,我拙笔写生活,写认知,倾泻自己的心灵之泉,终于,有小文见诸报刊。那一篇篇文字,是我生活的万花筒,是我前行的冲锋号。
“虫声窗外月,书册夜深灯。”在寂寞中寂寞阅读,在寂寞中碰撞寂寞火花,在寂寞中衍生寂寞绮梦,寂寞开辟宏阔天地。
懵懵懂懂、浮皮潦草阅读大部头小说,是上初中的时候。现在都记不清了,那两本破书《安娜·卡列尼娜》《薛仁贵征东》何处得来。虽然破损凋敝,我一直视为至宝,不离不弃,珍藏在家。后来,《安娜·卡列尼娜》竟成了我一段寂寥时光的亲密伴侣。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忝列民办教师行列,任教初一语文。学校坐落在僻壤山区,小学一至五年级附设一班初中一年级,九个教师只我一人住校,放学之后和节假日,偌大的地方,只有我形影相吊、顾影自怜。白天孤单寂寥尚且好熬,夜晚更兼恐惧。窗外的小山,坟冢遍地,山林阴森,黑魆魆的是一个鬼魅世界。风吹山林,声音凄厉、古怪,简直是一部放大版的《聊斋志异》。
然而,命运给我关闭了一道门,又给我开了一扇窗,让我养成了读书的好习惯。那时,农村根本找不到买书的地方,好在,我还有一本《安娜·卡列尼娜》。我像个幽居仙道,在死寂中一遍复一遍地阅读,越读越投入,越读越生趣,越读越喜欢外表美丽、情感真诚、内心丰富、充满生命活力的年轻女人——安娜·卡列尼娜。我紧紧地缠在她身边,我赞赏她拼死追求幸福的可贵精神,同情她被上流社会逼到卧轨自杀的悲惨人生。除了这个主要人物之外,书中还描写了一百多个人物,这个庞大的形象体系拼凑出来的政治、经济、社会、宗教、道德、教育诸多领域的一幅幅精彩画面,无不紧扣心弦,将我带到十九世纪中叶既陌生又似曾相识的异国他乡——俄国。《安娜·卡列尼娜》给我铸成一层五彩斑斓的硬壳,将孤独、寂寞、恐惧拒之房门以外,拒之心门以外。
后来,有领导看重我逆袭超人的顽强韧性,破格提拔我到教育领导岗位,肩膺全镇教育领导和管理工作。这个岗位事务繁冗,上面一根针下面千条线,我成天忙忙碌碌,应付工作。在教师面前,我表面乔装伟岸和冷傲,但背后心灵寂寞,产生迷失方向的隐忧,担心丢失自我,过去那个爱读书的“仙道”还能回归吗?我无处可逃。我时常回味过去,寻觅生命足迹,捕捉历史跫音。我禅悟反省,渐渐淡看浮华,“偷得浮生半日闲”,挤时间、瞅机会。更多的是夜读,看月华如水,星光熠熠;听蛩吟虫鸣,窃窃私语;展卷书帙,浅尝深品。不闻喧嚣事,不念无情人,于月光中,只有书香入怀。有了古今中外书香滋养,心灵逐渐清雅淡泊,开阔平和。曾见过一句话,我印象深刻:“我打开一本书,一个灵魂就苏醒。”
退休后,老伴到千里之外连云港的女儿家带外孙,我留守在家照顾老娘。老娘人老恋旧,坚守乡下故土不肯离去,我也只好屈身在没有隔间的小屋里陪伴。因怕打扰患有心脏病的老娘,小屋里没有电视,没有广播,唯有书香四溢,《唐宋词鉴赏辞典》《唐诗三百首》《飘》《悲惨世界》《简·爱》,还有获得第八、第九届茅盾文学奖的几部长篇,码在单身小床后沿,一道窄窄的“书墙”,是陋室一道别致的儒雅风景。有书香,不寂寞。夜深人静,月落梧桐,窗外落叶沙沙,屋内青灯幽幽,清凉空气透过窗棂,与暖暖的书香邂逅,我尽情地涵泳其中,沉醉其中,心里始终温暖,始终芬芳。
在一天天平淡的日子里,在一缕缕流连的月华里,十年幽居,十年阅读,十年冲动,十年尝试,我拙笔写生活,写认知,倾泻自己的心灵之泉,终于,有小文见诸报刊。那一篇篇文字,是我生活的万花筒,是我前行的冲锋号。
“虫声窗外月,书册夜深灯。”在寂寞中寂寞阅读,在寂寞中碰撞寂寞火花,在寂寞中衍生寂寞绮梦,寂寞开辟宏阔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