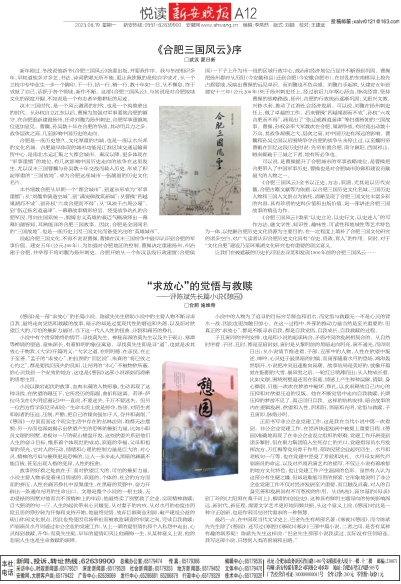发布日期:
“求放心”的觉悟与救赎
《憩园》是一部“求放心”的长篇小说。陈斌先先生借助小说中的主要人物不断寻求自我、最终走向觉悟和救赎的故事,暗示的却是过度现代性的窘迫和失落,以及面对欲望巨大的、可怕的摧折力量时,当下这一代人人性的扭曲、分裂和痛苦的挣扎。
小说中有个贯穿始终的情节:寻找莫先生。神秘高深的莫先生以及关于砚山、寒潭等禅境的塑造,意味深长,有着鲜明的象征寓意。寻找莫先生即是寻“道”,也就是求其放心于物我。《大学》开篇明义:“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孟子的“求放心”、柏拉图的“回忆说”、朱熹的“将已放之心约之”,都是要找回丧失的良知,让光明的“本心”不被物欲所蔽,给心灵找到一个安放的地方,这也是《憩园》这部小说深刻而清晰的思想主旨。
小说以跌宕起伏的故事、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生动再现了这种寻找,在欲望的碾压下,它所经历的陷溺、曲折和迷离。若泽·萨拉马戈在《失明症漫记》中一直说,不要迷失,千万不要迷失。但另一位西方哲学家尼采却说:“生命本质上就是掠夺、伤害,对陌生者和弱者的压迫、压制、严酷,把自己的倾向强加于人,吞并和剥削。”《憩园》一方面直面这个现实生活中存在的丛林法则,谁都无法摆脱;另一方面也深刻揭示出欲望产生的恐怖的摧折力量,比如小职员文璟的别墅,老板句一厅的砚山楼盘开发,这些欲望关系到他们人生的奋斗目标,维系着个体现世的成功、家庭的幸福、父母和祖辈的荣光,它对人的行动、情绪和心理的控制力量是巨大的,对心灵、精神的污染与摧残更是恐怖的,让人一步步走入黑暗的渊薮不能自拔,甚至出现人格的变异、人性的扭曲。
故事的好看之处就在于,面对欲望巨大的、可怕的摧折力量,小说主要人物承受着来自情感的、家庭的、个体的、社会的方方面面的挤压,人性在痛苦挣扎中涅槃重生,在黑暗的荒野中,奋力开辟出一条通向光明的生命出口。文璟是整个小说的一根主线,无功受禄的别墅对他而言不啻精神上的牢房,他最终卖了别墅救了企业,实现精神救赎;自大猥琐的句一厅,人生的起伏带来心灵嬗变,从对妻子的内疚,从对水月的态度由阴险丑恶的狰狞转为忏悔和支持开始,他最终觉悟,放弃巨额商业利润,破产建设公益的砚山休闲文化景点,因此也免受因官场牵扯而被收监调查的牢狱之灾,完成自我救赎;庐剧演员水月则通过非公企业的党建工作,从上一辈的爱恨情仇和个人私怨中走出,心灵得到救赎、升华;而莫先生呢,早年的爱情幻灭让他痛悔一生,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悲剧人生也是生命救赎的演绎。
小说中的人物为了追寻的目标穷尽鲜血和泪水,而觉悟与救赎无一不是心灵的背水一战,因此也更加触目惊心。在这一过程中,外部的推动力量当然是至关重要的,但真正的“求放心”,都是不断寻求自我,都是自我觉悟、自我成长、自我救赎的过程。
子丑寅卯的序列安排,也是和小说的起承转合、矛盾冲突的发展相契合的。从自然时序看,子时、丑时,都是至暗时刻,寅时是从黎明前的黑暗走向明亮,寅不通光,而卯则日出;从小说情节推进看,子部、丑部中的人物,人性在欲望中叛逆、呻吟,心灵处于最黑暗的时候,而寅部随着水月的登场,鸿沟轰然裂开,小说把冲突迅速推向高潮。故事结局是美好的,就像开篇就在酝酿的大雪,暴风雪之后,一轮红日喷薄而出;从人物成长看,比如文璟,围绕别墅退还而在家庭、情感上产生种种误解、猜疑,身心撕裂,只能一次次在梦游中破坏、挣扎,以此来释放自己内心的压抑和对欲望压迫的反叛。他在不断觉悟中走向自我救赎,长期压抑的梦游不见了,真正回归自我。这样的结构安排,暗合故事的内在逻辑发展,欲望和人性,阴和阳,黑暗和光明,觉悟与救赎,子丑寅卯,脉络分明。
正面书写非公企业党建工作,这是我在当代小说中第一次看到。非公企业党建工作,在经济快速发展中被提上重要日程。《憩园》准确地再现了在非公企业设立组织的艰难,党建工作开展受到诸多掣肘,但在聚力集团陷入生死存亡的关口,党建指导员水月发挥沈方、万红梅等党员骨干作用,帮助民营企业起死回生。水月和老板句一厅等,也在党建中经受了考验和洗礼。水月母女两代庐剧演员的命运,以及对庐剧表演艺术的描写,不仅让小说有着浓郁的地方文化特色,也让党建工作产生温润的色彩。虽然有人认为这部分有生硬之嫌,但却是难能可贵的探索,它形象地说明了非公企业党建工作不仅对经济发展至关重要,而且触及灵魂,对人的自身完善和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从《铁流》、高尔基的《母亲》到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柳青的《创业史》,这种具有鲜明主题导向的传统影响深远,新时代、新征程,需要文学艺术更好地同频共振,从这个意义上说,《憩园》对此是一种守正创新,也是作家回应时代需求的一种智慧。
最后一点,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巴金先生有两部名著:《寒夜》《憩园》,而今陈斌先先生除了《憩园》,还写过《寒腔》《寒砚》《寒沙》三部中篇小说,二者之间,是否有某种有趣的联系呢?陈斌先先生这样说:“巴金先生那部小说我读过,实际没有任何暗连。我写这部小说,只想到人类的困境和出路。”
小说中有个贯穿始终的情节:寻找莫先生。神秘高深的莫先生以及关于砚山、寒潭等禅境的塑造,意味深长,有着鲜明的象征寓意。寻找莫先生即是寻“道”,也就是求其放心于物我。《大学》开篇明义:“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孟子的“求放心”、柏拉图的“回忆说”、朱熹的“将已放之心约之”,都是要找回丧失的良知,让光明的“本心”不被物欲所蔽,给心灵找到一个安放的地方,这也是《憩园》这部小说深刻而清晰的思想主旨。
小说以跌宕起伏的故事、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生动再现了这种寻找,在欲望的碾压下,它所经历的陷溺、曲折和迷离。若泽·萨拉马戈在《失明症漫记》中一直说,不要迷失,千万不要迷失。但另一位西方哲学家尼采却说:“生命本质上就是掠夺、伤害,对陌生者和弱者的压迫、压制、严酷,把自己的倾向强加于人,吞并和剥削。”《憩园》一方面直面这个现实生活中存在的丛林法则,谁都无法摆脱;另一方面也深刻揭示出欲望产生的恐怖的摧折力量,比如小职员文璟的别墅,老板句一厅的砚山楼盘开发,这些欲望关系到他们人生的奋斗目标,维系着个体现世的成功、家庭的幸福、父母和祖辈的荣光,它对人的行动、情绪和心理的控制力量是巨大的,对心灵、精神的污染与摧残更是恐怖的,让人一步步走入黑暗的渊薮不能自拔,甚至出现人格的变异、人性的扭曲。
故事的好看之处就在于,面对欲望巨大的、可怕的摧折力量,小说主要人物承受着来自情感的、家庭的、个体的、社会的方方面面的挤压,人性在痛苦挣扎中涅槃重生,在黑暗的荒野中,奋力开辟出一条通向光明的生命出口。文璟是整个小说的一根主线,无功受禄的别墅对他而言不啻精神上的牢房,他最终卖了别墅救了企业,实现精神救赎;自大猥琐的句一厅,人生的起伏带来心灵嬗变,从对妻子的内疚,从对水月的态度由阴险丑恶的狰狞转为忏悔和支持开始,他最终觉悟,放弃巨额商业利润,破产建设公益的砚山休闲文化景点,因此也免受因官场牵扯而被收监调查的牢狱之灾,完成自我救赎;庐剧演员水月则通过非公企业的党建工作,从上一辈的爱恨情仇和个人私怨中走出,心灵得到救赎、升华;而莫先生呢,早年的爱情幻灭让他痛悔一生,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悲剧人生也是生命救赎的演绎。
小说中的人物为了追寻的目标穷尽鲜血和泪水,而觉悟与救赎无一不是心灵的背水一战,因此也更加触目惊心。在这一过程中,外部的推动力量当然是至关重要的,但真正的“求放心”,都是不断寻求自我,都是自我觉悟、自我成长、自我救赎的过程。
子丑寅卯的序列安排,也是和小说的起承转合、矛盾冲突的发展相契合的。从自然时序看,子时、丑时,都是至暗时刻,寅时是从黎明前的黑暗走向明亮,寅不通光,而卯则日出;从小说情节推进看,子部、丑部中的人物,人性在欲望中叛逆、呻吟,心灵处于最黑暗的时候,而寅部随着水月的登场,鸿沟轰然裂开,小说把冲突迅速推向高潮。故事结局是美好的,就像开篇就在酝酿的大雪,暴风雪之后,一轮红日喷薄而出;从人物成长看,比如文璟,围绕别墅退还而在家庭、情感上产生种种误解、猜疑,身心撕裂,只能一次次在梦游中破坏、挣扎,以此来释放自己内心的压抑和对欲望压迫的反叛。他在不断觉悟中走向自我救赎,长期压抑的梦游不见了,真正回归自我。这样的结构安排,暗合故事的内在逻辑发展,欲望和人性,阴和阳,黑暗和光明,觉悟与救赎,子丑寅卯,脉络分明。
正面书写非公企业党建工作,这是我在当代小说中第一次看到。非公企业党建工作,在经济快速发展中被提上重要日程。《憩园》准确地再现了在非公企业设立组织的艰难,党建工作开展受到诸多掣肘,但在聚力集团陷入生死存亡的关口,党建指导员水月发挥沈方、万红梅等党员骨干作用,帮助民营企业起死回生。水月和老板句一厅等,也在党建中经受了考验和洗礼。水月母女两代庐剧演员的命运,以及对庐剧表演艺术的描写,不仅让小说有着浓郁的地方文化特色,也让党建工作产生温润的色彩。虽然有人认为这部分有生硬之嫌,但却是难能可贵的探索,它形象地说明了非公企业党建工作不仅对经济发展至关重要,而且触及灵魂,对人的自身完善和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从《铁流》、高尔基的《母亲》到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柳青的《创业史》,这种具有鲜明主题导向的传统影响深远,新时代、新征程,需要文学艺术更好地同频共振,从这个意义上说,《憩园》对此是一种守正创新,也是作家回应时代需求的一种智慧。
最后一点,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巴金先生有两部名著:《寒夜》《憩园》,而今陈斌先先生除了《憩园》,还写过《寒腔》《寒砚》《寒沙》三部中篇小说,二者之间,是否有某种有趣的联系呢?陈斌先先生这样说:“巴金先生那部小说我读过,实际没有任何暗连。我写这部小说,只想到人类的困境和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