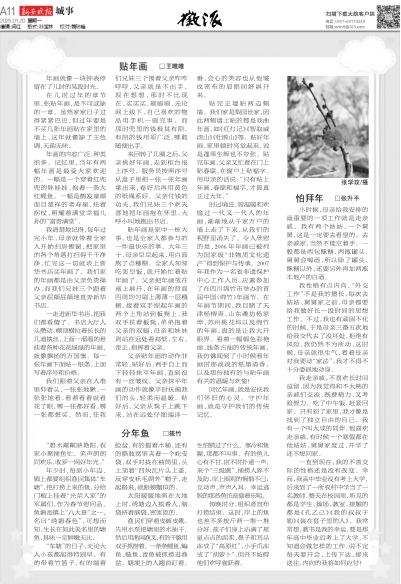发布日期:
贴年画
年画就像一块钟表停留在了儿时的某段时光。
在儿时过年的章节里,张贴年画,是不可或缺的一章。虽然家家日子过得紧紧巴巴,但过年要是不买几张年画贴在家里的墙上,这年就像缺了主色调,无韵无味。
年画的内容广泛,种类很多。记忆里,当年有两幅年画是最受大家欢迎的。一幅是一个穿着红兜兜的胖娃娃,抱着一条大红鲤鱼。一幅是鹤发童颜面目慈祥的老寿星,拄着拐杖,照耀着满堂幸福儿孙的“富贵满堂”。
我清楚地记得,每年过完小年,母亲就带着全家人开始扫房擦窗,把家里的各个角落打扫得干干净净,忙完这一切就该上新华书店买年画了。我们家的年画都是由父亲负责操办,而我们兄妹三个跟着父亲屁颠屁颠地直奔新华书店。
一走进新华书店,把我们都看傻了。书店大厅人头攒动,棚顶横拉着长长的几道铁丝,上面一溜溜的悬挂着各种花花绿绿的年画,就像飘扬的万国旗。每一张年画下面贴一纸条,上面写着序号和价格。
我们跟着父亲在人堆里仰着头,一张张地瞅,一张张地看,看着看着就看花了眼,哪一张都好看,哪一张都想买。然而,任我们兄妹三个围着父亲咋咋呼呼,父亲就是不出手。现在想想,那时不比现在,买买买,刷刷刷,无论网上线下,自己喜欢的物品用手机一刷完事。而那时兜里的钱极其有限,有限的钱用项广泛,哪敢随便出手。
来回转了几圈之后,父亲挑好年画,走到柜台报上序号。服务员按照序号从盒子里把一张一张年画拿出来,卷好后再用黄色的纸绳系好。父亲付钱的功夫,我们兄妹三个欢天喜地把年画抱在怀里,大呼小叫地跑出书店。
贴年画是家中一桩大事,也是全家人都参与的一件最快乐的事。大年三十,母亲早早起来,用白面熬了点糨糊。全家人匆匆吃罢早饭,就开始忙着贴年画了。父亲把年画放在桌上展开,在年画的背面四周均匀刷上薄薄一层糨糊,接着双手捏起年画的两个上角站到板凳上,我双手扶着板凳,弟弟抱着父亲的双腿,母亲和妹妹则站在远处看高低、左右、歪正,指挥着父亲。
父亲贴年画的动作非常轻,贴好后,两手自上而下轻轻抹平年画,直到没有一丝皱纹。父亲抹平年画的动作就像平时抚摸我们的头,轻柔而温暖。贴好后,父亲从凳子上跳下来,站在远处仔细端详一番,会心的笑容也从他皱纹密布的眉眼间舒展开来。
贴完正墙贴两边侧墙。我们家是梨园世家,因此两侧墙上贴的都是戏曲年画,如《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杜鹃山》等。贴好年画,家里顿时亮堂起来,说是蓬荜生辉也不夸张。贴完年画,父亲又忙着在门上贴春联,在窗户上贴福字。用母亲的话说:“只有贴上年画、春联和福字,才算真正过大年。”
时过境迁,曾温暖和欢愉过一代又一代人的年画,渐渐地从千家万户的墙上走了下来,从我们的视野里消失了。令人欣慰的是,2006年年画已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保护与传承。2007年我作为一名省非遗保护中心工作人员,应邀参加了在四川绵竹市举办的首届中国(绵竹)年画节。在年画节期间,我目睹了天津杨柳青、山东潍坊杨家埠、苏州桃花坞以及绵竹的年画,真的是让我大开眼界。看着一幅幅色彩艳丽、线条古拙的传统年画,我仿佛闻到了小时候看年画时那淡淡的纸墨清香,以及那份独有的与贴年画有关的温暖与欢愉!
回忆年画,就是安抚我们怀旧的心灵。守护年画,就是守护我们的传统记忆。
在儿时过年的章节里,张贴年画,是不可或缺的一章。虽然家家日子过得紧紧巴巴,但过年要是不买几张年画贴在家里的墙上,这年就像缺了主色调,无韵无味。
年画的内容广泛,种类很多。记忆里,当年有两幅年画是最受大家欢迎的。一幅是一个穿着红兜兜的胖娃娃,抱着一条大红鲤鱼。一幅是鹤发童颜面目慈祥的老寿星,拄着拐杖,照耀着满堂幸福儿孙的“富贵满堂”。
我清楚地记得,每年过完小年,母亲就带着全家人开始扫房擦窗,把家里的各个角落打扫得干干净净,忙完这一切就该上新华书店买年画了。我们家的年画都是由父亲负责操办,而我们兄妹三个跟着父亲屁颠屁颠地直奔新华书店。
一走进新华书店,把我们都看傻了。书店大厅人头攒动,棚顶横拉着长长的几道铁丝,上面一溜溜的悬挂着各种花花绿绿的年画,就像飘扬的万国旗。每一张年画下面贴一纸条,上面写着序号和价格。
我们跟着父亲在人堆里仰着头,一张张地瞅,一张张地看,看着看着就看花了眼,哪一张都好看,哪一张都想买。然而,任我们兄妹三个围着父亲咋咋呼呼,父亲就是不出手。现在想想,那时不比现在,买买买,刷刷刷,无论网上线下,自己喜欢的物品用手机一刷完事。而那时兜里的钱极其有限,有限的钱用项广泛,哪敢随便出手。
来回转了几圈之后,父亲挑好年画,走到柜台报上序号。服务员按照序号从盒子里把一张一张年画拿出来,卷好后再用黄色的纸绳系好。父亲付钱的功夫,我们兄妹三个欢天喜地把年画抱在怀里,大呼小叫地跑出书店。
贴年画是家中一桩大事,也是全家人都参与的一件最快乐的事。大年三十,母亲早早起来,用白面熬了点糨糊。全家人匆匆吃罢早饭,就开始忙着贴年画了。父亲把年画放在桌上展开,在年画的背面四周均匀刷上薄薄一层糨糊,接着双手捏起年画的两个上角站到板凳上,我双手扶着板凳,弟弟抱着父亲的双腿,母亲和妹妹则站在远处看高低、左右、歪正,指挥着父亲。
父亲贴年画的动作非常轻,贴好后,两手自上而下轻轻抹平年画,直到没有一丝皱纹。父亲抹平年画的动作就像平时抚摸我们的头,轻柔而温暖。贴好后,父亲从凳子上跳下来,站在远处仔细端详一番,会心的笑容也从他皱纹密布的眉眼间舒展开来。
贴完正墙贴两边侧墙。我们家是梨园世家,因此两侧墙上贴的都是戏曲年画,如《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杜鹃山》等。贴好年画,家里顿时亮堂起来,说是蓬荜生辉也不夸张。贴完年画,父亲又忙着在门上贴春联,在窗户上贴福字。用母亲的话说:“只有贴上年画、春联和福字,才算真正过大年。”
时过境迁,曾温暖和欢愉过一代又一代人的年画,渐渐地从千家万户的墙上走了下来,从我们的视野里消失了。令人欣慰的是,2006年年画已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保护与传承。2007年我作为一名省非遗保护中心工作人员,应邀参加了在四川绵竹市举办的首届中国(绵竹)年画节。在年画节期间,我目睹了天津杨柳青、山东潍坊杨家埠、苏州桃花坞以及绵竹的年画,真的是让我大开眼界。看着一幅幅色彩艳丽、线条古拙的传统年画,我仿佛闻到了小时候看年画时那淡淡的纸墨清香,以及那份独有的与贴年画有关的温暖与欢愉!
回忆年画,就是安抚我们怀旧的心灵。守护年画,就是守护我们的传统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