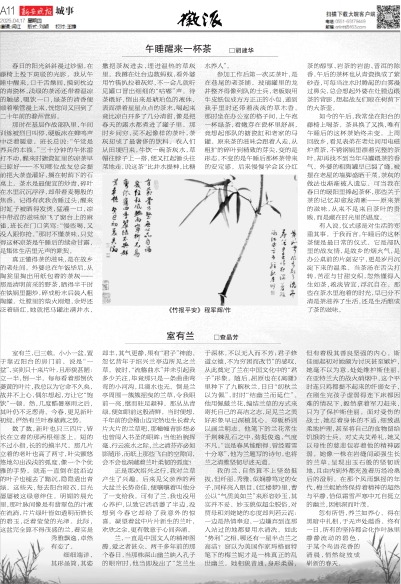发布日期:
午睡醒来一杯茶
春日的阳光斜斜漫过纱窗,在藤椅上投下斑驳的光影。我从午睡中醒来,口干舌燥间,摸到枕边的青瓷杯,浅绿的茶汤还带着温凉的触感,啜饮一口,绿茶的清香便顺着喉管漫上来,恍惚间又回到了二十年前的滁州营房。
那时在基层作战部队里,午间训练被烈日叫停,硬板床在蝉鸣声中泛着暖意。班长总说:“午觉是养兵的本钱。”三十分钟的午休雷打不动,醒来时搪瓷缸里的凉茶早已晾好——不知哪位战友总会提前把大茶壶灌好,搁在树荫下的石桌上。茶水是最便宜的炒青,碎叶在水里沉沉浮浮,却带着麦穗般的焦香。记得有次我贪睡过头,醒来时缸子被晒得发烫,猛灌一口,凉中带涩的滋味惊飞了窗台上的麻雀,班长在门口笑骂:“慢些喝,又没人跟你抢。”那时不懂茶味,只觉得这杯凉茶是午睡后的续命甘露,是集体生活里无声的默契。
真正懂得茶的滋味,是在故乡的老灶间。外婆总在午饭毕后,从陶瓮里掏出用纸包着的茶灰——那是清明前采的野茶,晒得半干时在铁锅里翻炒,碎成粉末后装入粗陶罐。灶膛里的柴火刚熄,余烬还泛着暗红,她就把马罐注满井水,撒把茶灰进去,埋进温热的草灰里。我蹲在灶台边数蚂蚁,看外婆用竹筷扒拉着灰烬,不一会儿就听见罐口冒出细细的“咕嘟”声。待茶煨好,倒出来是琥珀色的液体,表面漂着星星点点的茶末,喝起来竟比凉白开多了几分清甜,像是把春天的露水都煮进了罐子里。那时乡间穷,买不起像样的茶叶,茶灰却成了最奢侈的饮料。农人们从田埂归来,牛饮一碗茶灰水,草帽往脖子上一搭,便又扛起锄头往菜地走,说这茶“比井水提神,比糖水养人”。
参加工作后第一次买茶叶,是在巷尾的老茶铺。玻璃罐里的龙井整齐得像列队的士兵,老板娘用牛皮纸包成方方正正的小包,递到我手里时还带着淡淡的草木香。那时坐在办公室的格子间,上午泡一杯绿茶,看嫩芽在瓷杯里舒展,竟想起部队的搪瓷缸和老家的马罐。原来茶的滋味会跟着人走,从粗犷的碎叶到精致的芽尖,变的是形态,不变的是午睡后那杯茶带来的安定感。后来慢慢学会区分红茶的醇厚、岩茶的岩韵、普洱的陈香,午后的茶杯也从青瓷换成了紫砂壶,可每当注水时腾起的白雾漫过鼻尖,总会想起外婆在灶膛边煨茶的背影,想起战友们晾在树荫下的大茶壶。
如今的午后,我常坐在阳台的藤椅上喝茶。茶具换了又换,唯有午睡后的这杯茶始终未变。上周回故乡,看见表弟在老灶间用电磁炉煮茶,不锈钢锅里漂着完整的茶叶,却再找不到当年马罐煨茶的香气。外婆的粗陶罐早已裂了缝,被摆在老屋的墙脚盛晒干菜,茶灰的做法也渐渐被人遗忘。可当我在春日的暖阳里捧起茶杯,那些关于茶的记忆却愈发清晰——原来茶的滋味,从来不是来自茶叶的贵贱,而是藏在时光里的温度。
有人说,仪式感是对生活的郑重其事。于我而言,午睡后的这杯茶便是最日常的仪式。它是部队里的战友情,是故乡的烟火气,是办公桌前的片刻安宁,更是岁月沉淀下来的温柔。当茶汤在舌尖打转,苦涩与甘甜交织,忽然懂得人生如茶,浓淡皆宜,浮沉自在。那些在茶水里泡着的时光,早已分不清是茶滋养了生活,还是生活酿成了茶的滋味。
那时在基层作战部队里,午间训练被烈日叫停,硬板床在蝉鸣声中泛着暖意。班长总说:“午觉是养兵的本钱。”三十分钟的午休雷打不动,醒来时搪瓷缸里的凉茶早已晾好——不知哪位战友总会提前把大茶壶灌好,搁在树荫下的石桌上。茶水是最便宜的炒青,碎叶在水里沉沉浮浮,却带着麦穗般的焦香。记得有次我贪睡过头,醒来时缸子被晒得发烫,猛灌一口,凉中带涩的滋味惊飞了窗台上的麻雀,班长在门口笑骂:“慢些喝,又没人跟你抢。”那时不懂茶味,只觉得这杯凉茶是午睡后的续命甘露,是集体生活里无声的默契。
真正懂得茶的滋味,是在故乡的老灶间。外婆总在午饭毕后,从陶瓮里掏出用纸包着的茶灰——那是清明前采的野茶,晒得半干时在铁锅里翻炒,碎成粉末后装入粗陶罐。灶膛里的柴火刚熄,余烬还泛着暗红,她就把马罐注满井水,撒把茶灰进去,埋进温热的草灰里。我蹲在灶台边数蚂蚁,看外婆用竹筷扒拉着灰烬,不一会儿就听见罐口冒出细细的“咕嘟”声。待茶煨好,倒出来是琥珀色的液体,表面漂着星星点点的茶末,喝起来竟比凉白开多了几分清甜,像是把春天的露水都煮进了罐子里。那时乡间穷,买不起像样的茶叶,茶灰却成了最奢侈的饮料。农人们从田埂归来,牛饮一碗茶灰水,草帽往脖子上一搭,便又扛起锄头往菜地走,说这茶“比井水提神,比糖水养人”。
参加工作后第一次买茶叶,是在巷尾的老茶铺。玻璃罐里的龙井整齐得像列队的士兵,老板娘用牛皮纸包成方方正正的小包,递到我手里时还带着淡淡的草木香。那时坐在办公室的格子间,上午泡一杯绿茶,看嫩芽在瓷杯里舒展,竟想起部队的搪瓷缸和老家的马罐。原来茶的滋味会跟着人走,从粗犷的碎叶到精致的芽尖,变的是形态,不变的是午睡后那杯茶带来的安定感。后来慢慢学会区分红茶的醇厚、岩茶的岩韵、普洱的陈香,午后的茶杯也从青瓷换成了紫砂壶,可每当注水时腾起的白雾漫过鼻尖,总会想起外婆在灶膛边煨茶的背影,想起战友们晾在树荫下的大茶壶。
如今的午后,我常坐在阳台的藤椅上喝茶。茶具换了又换,唯有午睡后的这杯茶始终未变。上周回故乡,看见表弟在老灶间用电磁炉煮茶,不锈钢锅里漂着完整的茶叶,却再找不到当年马罐煨茶的香气。外婆的粗陶罐早已裂了缝,被摆在老屋的墙脚盛晒干菜,茶灰的做法也渐渐被人遗忘。可当我在春日的暖阳里捧起茶杯,那些关于茶的记忆却愈发清晰——原来茶的滋味,从来不是来自茶叶的贵贱,而是藏在时光里的温度。
有人说,仪式感是对生活的郑重其事。于我而言,午睡后的这杯茶便是最日常的仪式。它是部队里的战友情,是故乡的烟火气,是办公桌前的片刻安宁,更是岁月沉淀下来的温柔。当茶汤在舌尖打转,苦涩与甘甜交织,忽然懂得人生如茶,浓淡皆宜,浮沉自在。那些在茶水里泡着的时光,早已分不清是茶滋养了生活,还是生活酿成了茶的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