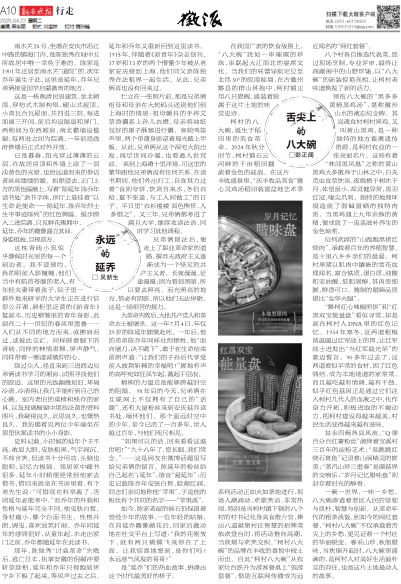发布日期:
永远的延乔
南水关28号,坐落在安庆市沿江中路的镇海门内,是陈独秀在城中五所故居中唯一幸免于难的。陈家是1901年迁居至南水关“道院”的,次年乔年诞生于此,这里是延年、乔年兄弟俩接受国学启蒙教育的地方。
这是一栋晚清民居建筑,坐北朝南,穿枋式木制构架、硬山式屋顶、小青瓦合瓦屋面,共四进三院,每进面阔三开间,前后均设隔扇和屏门,两稍间为东西厢房,南北檐墙设槛窗;每两进之间为院落,一年前经政府修缮后正式对外开放。
已是暮春,阳光穿过薄薄的云层,在故居房顶和外墙上涂了一层浅黄色的光晕,也给远道而来的参访者丝丝缕缕的暖。抬眼望去,正门上方的黑色匾额上,写着“陈延年陈乔年读书处”隶书字体,序厅上悬挂着“以生命赴使命——陈延年、陈乔年烈士生平事迹陈列”的红色牌匾。缓步跨入二进院落,只见鲜花簇拥中,延年、乔年的雕像矗立其间,身姿挺拔、目视前方。
这栋青砖小筑似乎静候时光里的每一个到访者。我不曾预约,我的眼前人影幢幢,他们当中有皓首苍颜的老人,有年轻夫妻带着孩子,院子里一群外地来研学的大学生正在进行信仰公开课,展柜里泛黄的《新青年》复刻本,历史褶皱里的青年身影,此刻在二十一世纪的春风里重叠……人们从不同的地方而来,或擦肩而过,或彼此交汇。同样踩着脚下的青砖,同样的神情肃穆,屏声静气,同样带着一颗虔诚敬仰的心。
绕过众人,径直来到三进西边兄弟俩读书学习的厢房,试图寻找他们的踪迹。这里的光线幽微如旧,环境冷清,冷清得让我几乎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室内老旧的桌椅和残存的家具,以及玻璃橱窗中那些泛黄的资料图片,我凝视良久,沉思良久,也慨然良久。我仿佛看见两位少年端坐在那里伏案读书的小小身影。
史料记载,小时候的延年个子不高,浓眉大眼,皮肤粗黑,气宇深沉,不苟言笑,但读书十分用功,头脑也聪明,记忆力极强。邻居家中藏书很多,延年小时候便经常到他家去借书,借回来就坐在书房里看,有个老先生说:“可惜现在科举废了,否则延年必能考中。”而乔年的外貌和性格与延年完全不同,他皮肤白皙,身材瘦小,像个白面书生。性格开朗、调皮,喜欢说笑打闹。乔年同延年的感情很好,从童年起,未走出家门之前,乔年都随延年在此读书。
那年,陈独秀“讨袁革命”失败后,逃亡日本,执掌安徽的倪嗣冲要斩草除根,延年和乔年只得跑到怀宁乡下躲了起来,等风声过去之后,延年和乔年又重新回到这里读书。1915年,伴随着《新青年》杂志创刊,17岁和13岁的两个懵懂少年被从老家安庆接到上海,他们同父亲陈独秀在法租界一起生活。从此,兄弟俩再也没有回来过。
伫立在一张照片前,那是兄弟俩祖母和母亲在大轮码头送别他们到上海时的情景:祖母颤抖的手将艾草香囊系上孙儿衣襟,母亲将油纸包好的墨子酥塞进行囊。客轮鸣笛声里,两个单薄身影逆着晨光踏上甲板。从此,兄弟俩从这个深宅大院出发,阅尽世间冷暖,也看透人世荒凉。来到上海滩十里洋场,可这里的繁华跟他兄弟俩没有任何关系,在读书期间,他们外出打工,自食其力过着“食则夸饼,饮则自来水,冬仍衣袷,夏不张盖,与工人同做工”的日子。平日里“衣衫褴褛面色憔悴,人多惜之”。又三年,兄弟俩都考进了震旦大学,继续攻读法语,同时学习其他课程。兄弟俩留法后,便走上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摒弃无政府主义逐渐成为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长夜漫漫,征途漫漫;因为看到黑暗,所以要去照亮。而光照亮的地方,势必有阴影,所以他们无法停歇。这是一场艰苦的接力。
大革命失败后,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被屠杀。这一年7月4日,年仅29岁的陈延年慷慨赴死。一年后,他的弟弟陈乔年同样壮烈牺牲,他“面向屠刀、决不跪下”,敢于在生命结束前朗声道:“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的幸福吧!”掷地有声的高呼宛如狂风乍起,激起千层浪。
精神的力量总是能够跨越时空的阻隔。98年后的今天,兄弟俩在互联网上不仅拥有了自己的“话题”,还有大量粉丝来到安庆延乔读书处,缅怀他们。那个遥远时空中的少年,至今已活了一百多年,世人越过百年,与他们咫尺相见,
“如果可以的话,回来看看这盛世吧!”“九十八年了,您长眠,我们常念。”……这是网友在微博话题里写给兄弟俩的留言。陈延年的粉丝给自己起名“i延年”,谐音“爱延年”;历史记载陈乔年皮肤白皙,脸颊红润,同志们亲切地称他“苹果”,于是他的粉丝有个共同的名字——“苹果派”。
如今,陈家老屋的砖石仍保留着曾经少年的故事,一位年轻的姑娘,在向延乔雕像献花后,回家后激动地在社交平台上写道:“我的花刚放下,就有两只蝴蝶飞来停在了上面。让我惊喜地想到,是你们吗?永远意气风发的哥哥!”
是“延乔”们的热血故事,拼凑出这个时代最美好的样子。
这是一栋晚清民居建筑,坐北朝南,穿枋式木制构架、硬山式屋顶、小青瓦合瓦屋面,共四进三院,每进面阔三开间,前后均设隔扇和屏门,两稍间为东西厢房,南北檐墙设槛窗;每两进之间为院落,一年前经政府修缮后正式对外开放。
已是暮春,阳光穿过薄薄的云层,在故居房顶和外墙上涂了一层浅黄色的光晕,也给远道而来的参访者丝丝缕缕的暖。抬眼望去,正门上方的黑色匾额上,写着“陈延年陈乔年读书处”隶书字体,序厅上悬挂着“以生命赴使命——陈延年、陈乔年烈士生平事迹陈列”的红色牌匾。缓步跨入二进院落,只见鲜花簇拥中,延年、乔年的雕像矗立其间,身姿挺拔、目视前方。
这栋青砖小筑似乎静候时光里的每一个到访者。我不曾预约,我的眼前人影幢幢,他们当中有皓首苍颜的老人,有年轻夫妻带着孩子,院子里一群外地来研学的大学生正在进行信仰公开课,展柜里泛黄的《新青年》复刻本,历史褶皱里的青年身影,此刻在二十一世纪的春风里重叠……人们从不同的地方而来,或擦肩而过,或彼此交汇。同样踩着脚下的青砖,同样的神情肃穆,屏声静气,同样带着一颗虔诚敬仰的心。
绕过众人,径直来到三进西边兄弟俩读书学习的厢房,试图寻找他们的踪迹。这里的光线幽微如旧,环境冷清,冷清得让我几乎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室内老旧的桌椅和残存的家具,以及玻璃橱窗中那些泛黄的资料图片,我凝视良久,沉思良久,也慨然良久。我仿佛看见两位少年端坐在那里伏案读书的小小身影。
史料记载,小时候的延年个子不高,浓眉大眼,皮肤粗黑,气宇深沉,不苟言笑,但读书十分用功,头脑也聪明,记忆力极强。邻居家中藏书很多,延年小时候便经常到他家去借书,借回来就坐在书房里看,有个老先生说:“可惜现在科举废了,否则延年必能考中。”而乔年的外貌和性格与延年完全不同,他皮肤白皙,身材瘦小,像个白面书生。性格开朗、调皮,喜欢说笑打闹。乔年同延年的感情很好,从童年起,未走出家门之前,乔年都随延年在此读书。
那年,陈独秀“讨袁革命”失败后,逃亡日本,执掌安徽的倪嗣冲要斩草除根,延年和乔年只得跑到怀宁乡下躲了起来,等风声过去之后,延年和乔年又重新回到这里读书。1915年,伴随着《新青年》杂志创刊,17岁和13岁的两个懵懂少年被从老家安庆接到上海,他们同父亲陈独秀在法租界一起生活。从此,兄弟俩再也没有回来过。
伫立在一张照片前,那是兄弟俩祖母和母亲在大轮码头送别他们到上海时的情景:祖母颤抖的手将艾草香囊系上孙儿衣襟,母亲将油纸包好的墨子酥塞进行囊。客轮鸣笛声里,两个单薄身影逆着晨光踏上甲板。从此,兄弟俩从这个深宅大院出发,阅尽世间冷暖,也看透人世荒凉。来到上海滩十里洋场,可这里的繁华跟他兄弟俩没有任何关系,在读书期间,他们外出打工,自食其力过着“食则夸饼,饮则自来水,冬仍衣袷,夏不张盖,与工人同做工”的日子。平日里“衣衫褴褛面色憔悴,人多惜之”。又三年,兄弟俩都考进了震旦大学,继续攻读法语,同时学习其他课程。兄弟俩留法后,便走上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摒弃无政府主义逐渐成为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长夜漫漫,征途漫漫;因为看到黑暗,所以要去照亮。而光照亮的地方,势必有阴影,所以他们无法停歇。这是一场艰苦的接力。
大革命失败后,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被屠杀。这一年7月4日,年仅29岁的陈延年慷慨赴死。一年后,他的弟弟陈乔年同样壮烈牺牲,他“面向屠刀、决不跪下”,敢于在生命结束前朗声道:“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的幸福吧!”掷地有声的高呼宛如狂风乍起,激起千层浪。
精神的力量总是能够跨越时空的阻隔。98年后的今天,兄弟俩在互联网上不仅拥有了自己的“话题”,还有大量粉丝来到安庆延乔读书处,缅怀他们。那个遥远时空中的少年,至今已活了一百多年,世人越过百年,与他们咫尺相见,
“如果可以的话,回来看看这盛世吧!”“九十八年了,您长眠,我们常念。”……这是网友在微博话题里写给兄弟俩的留言。陈延年的粉丝给自己起名“i延年”,谐音“爱延年”;历史记载陈乔年皮肤白皙,脸颊红润,同志们亲切地称他“苹果”,于是他的粉丝有个共同的名字——“苹果派”。
如今,陈家老屋的砖石仍保留着曾经少年的故事,一位年轻的姑娘,在向延乔雕像献花后,回家后激动地在社交平台上写道:“我的花刚放下,就有两只蝴蝶飞来停在了上面。让我惊喜地想到,是你们吗?永远意气风发的哥哥!”
是“延乔”们的热血故事,拼凑出这个时代最美好的样子。